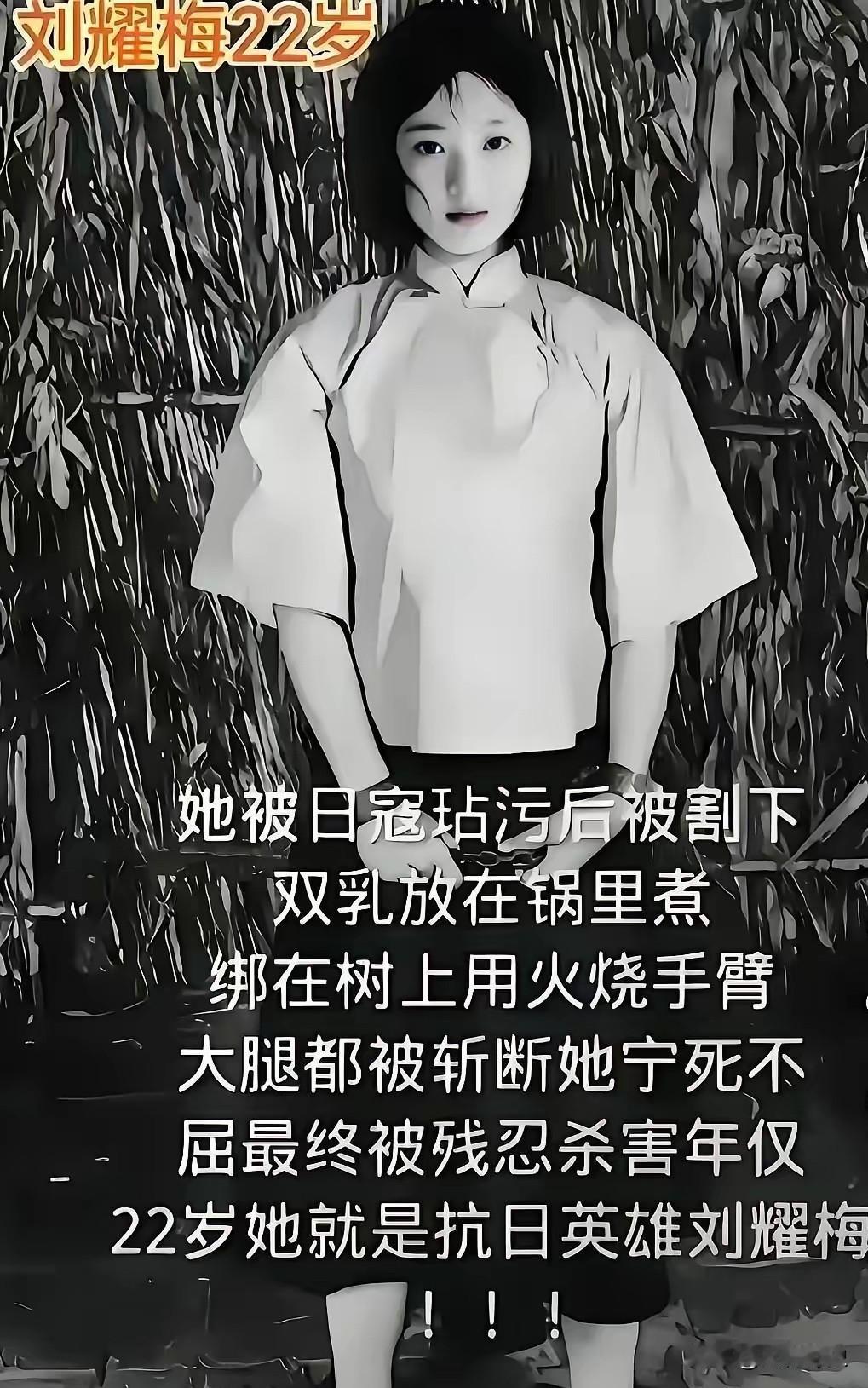1941年,八路军战士郑希和执行任务归来歇脚,竟撞见8名日军追逐农妇,他默默打开刺刀,孤身一人要迎击强敌? 郑希和,1919年生,寿光台头镇人,穷得念不起书,却跟着爷爷把八极拳练成了骨头里的狠劲。 搁1941年的鲁中荒坡上,风里都裹着硝烟和血腥味,谁也没料到,一个赶路歇脚的八路军战士,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农妇,攥紧了带刺刀的步枪,要跟八个全副武装的鬼子死拼。那年郑希和才22岁,身上的粗布军装沾着一路的泥土、草屑,还有几处被树枝划破的口子,手里的三八大盖是缴获的旧枪,枪身磨得发亮,可他眼里的狠劲,比刺刀还扎人——那不是鲁莽的冲动,是爷爷手把手教的八极拳练出的底气,是穷人家孩子在乱世里熬出的硬骨头,更是中国人见不得百姓受欺辱、见不得侵略者横行的血性,藏在骨头缝里,一触即发。 没人知道,郑希和的那身八极拳,是用苦日子熬出来的。寿光台头镇的盐碱地养人也磨人,1919年他出生时,家里穷得连块完整的床板都没有,更别说送他去读书,从小就跟着爷爷在田埂上、晒谷场练拳。爷爷是清末的老拳师,避战乱逃到台头镇,靠帮人护院、教邻里练拳糊口,一辈子没跟人争过强、斗过狠,却总跟郑希和说:“练拳不是为了打人逞强,是为了护自己、护弱小,见了恶人别怂,见了百姓受难别躲,这才是中国人的本分。” 郑希和性子闷,不爱说话,却把爷爷的话刻在了心里。从六岁起,天不亮就扎马步,一站就是两个时辰,腿麻得站不住也不敢挪;练冲拳、撞肩、缠腕,手心磨出厚厚的血痂,结痂了又磨破,直到长出一层硬茧;爷爷用青砖当靶子,让他练拳劲,一开始一拳下去青砖纹丝不动,胳膊震得发麻,他就天天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能一拳打碎青砖,八极拳的刚猛凌厉、一招制敌的狠劲,渐渐融进了他的骨子里。可乱世容不下安稳,1937年日军闯进寿光,烧杀抢掠,爷爷为了护着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被日军的刺刀挑死在晒谷场,临死前还攥着拳头,朝着日军的方向瞪着眼。那天,18岁的郑希和揣着一把爷爷留下的拳刺,看着被烧毁的房屋、死去的乡亲,眼里的泪混着怒火,一路辗转找到了八路军队伍,参军那天,他没说多余的话,只对着连长磕了三个响头:“我会打拳,能杀鬼子,能护着老百姓。” 参军后的郑希和,把八极拳的狠劲全用在了拼杀上。那会儿八路军装备落后,很多时候靠白刃战跟日军周旋,每次战斗,郑希和都冲在最前面,日军的刺刀再快,也快不过他八极拳的缠腕卸力;日军的力气再大,也扛不住他的撞肩顶肘,好几次白刃战,他一个人就能撂倒两三个日军,战友们都叫他“拳王战士”,都说“有郑希和在,白刃战就有底气”。可他从不炫耀,打完仗就默默收拾武器、照顾伤员,省下自己的干粮分给战友,依旧是那个闷不吭声、却浑身是劲的寿光汉子。 1941年秋,正是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清剿”最疯狂的日子,日军四处搜寻八路军的踪迹,烧村庄、抢粮食,还经常肆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那天,郑希和奉命去邻县侦察日军的部署,一路昼伏夜出,饿了就啃一口冻硬的窝头,渴了就喝一口山泉水,累得实在撑不住,才找了一处废弃的山神庙歇脚。他刚靠着山墙坐下,掏出怀里的窝头,还没来得及咬一口,就听见不远处的山沟里,传来农妇撕心裂肺的哭喊,还有日军的狞笑和呵斥声,那声音刺耳得很,像针一样扎在郑希和的心上。 他立刻握紧步枪,猫着腰,悄悄摸下山神庙,躲在一棵老槐树后面探头一瞧,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八个日军端着步枪,手里还拿着刺刀,正追逐着一个抱着襁褓的农妇。农妇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鞋子早就跑丢了,光着的脚被山路的石子划破,鲜血顺着脚趾缝往下淌,怀里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小脸憋得发紫。日军一边追,一边用生硬的中文咒骂,时不时开枪恐吓,子弹打在农妇身边的石头上,溅起一片片碎石,他们压根不是要抓农妇,就是在取乐,把百姓的苦难当成消遣,那嚣张跋扈的模样,跟当年杀害爷爷、残害乡亲的日军,一模一样。 郑希和的手攥得咯咯作响,指节泛白,悄悄拉开步枪的枪栓,“咔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山沟里格外清晰。他没有立刻冲出去,不是害怕,是在盘算——八个日军,个个全副武装,有步枪、有刺刀,而他只有一把旧步枪、一把刺刀,还有一身八极拳,硬拼肯定吃亏,八极拳讲究“出其不意、一招制敌”,得先偷袭,打乱日军的阵脚,再靠近身搏杀,拖延时间,也能护住农妇。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怒火,眼神变得格外沉着,一点点挪动身子,朝着日军的侧后方摸过去,指尖轻轻按住刺刀,缓缓打开,冰冷的刺刀,映着他眼里的怒火。 身边的草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农妇的哭喊越来越近,日军的狞笑也越来越近,郑希和猛地站起身,朝着离他最近的一名日军,纵身冲了过去。那名日军正低头嘲笑摔倒在地的农妇,压根没察觉到身后的危险,郑希和借着冲劲,一记八极拳的黑虎掏心,狠狠砸在日军的胸口,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