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中退出政坛,这一次为什么伤心绝望? 张亚中在10月19日深夜发布的那封长信,没有一句责怪,却句句是诀别。他没有说“我不玩了”,他说的是“我终究,不属于这里”。 这不是愤而离席,而是终于明白他守了三十年的灯塔,其实早就在党内无人问津。 2021年,他拿下六万票,32%的支持率,在党内掀起一阵“理念派”的风潮;四年后,只有2486票,连2%都不到。 他不是没努力,是这个党变了。他还站在原地,党却早已换了方向。那种落差,不只是数字的打击,更是一种存在感的消亡。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败选,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图证明理想还有市场。当结果揭晓的那一刻,所有坚持都变成了笑话。 他引用“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不是豪气冲天,而是自嘲。他知道,这次不是输了一个职务,而是彻底失去了参与这个游戏的意义。 很多人说他不懂选举,说他太理想主义,但问题不是他不懂,而是他不愿变。 他讲“统一”,讲“一中三宪”,讲签和平协议,这些在今天的国民党里,已经变成了过时的口号。 郑丽文讲“安居乐业”,讲“武统不是选项”,讲“务实路线”,她赢了,因为她懂得迎合。 张亚中不愿迎合。他还在坚持孙中山那一套“天下为公”,还在讲孙中山“统一是国民希望”的遗训。 今年三月,他在台北一手策划了孙中山逝世百年纪念活动,现场庄严肃穆,他眼里有光。但半年后,他却在同一个党内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古董”。 国民党这几年走得越来越快,但方向越来越模糊。朱立伦推“年轻化”,实则是切割“深蓝”; 郑丽文靠军系、眷村撑起来的选票,只是战术成功,不是理念胜利。 张亚中看得很清楚,选票背后没有认同,只有动员。他说这不是政党路线的胜利,是一次临时搭建的投票机器。 党内大佬的反应更是冷淡。马英九、朱立伦、韩国瑜,没有一个人对张亚中的理念表态。他们都祝贺郑丽文,却没人安慰张亚中。 这些年他在党内批评得罪了不少人,甚至骂朱立伦是“美国的线民”,但他从没背弃过自己的信仰。只是现在,他终于明白,这种信仰在这个党里已无用武之地。 张亚中不是不知道自己越来越边缘化。他知道郑丽文胜选,是靠组织,不是靠思想。他知道党内年轻人喜欢她的“战斗女神”形象,却不认同她的两岸立场。 他也知道,自己那一套哲学论述、历史脉络、制度设计,在这个时代显得太沉重,太复杂,太不讨喜。 他曾经试图用“教科书式”的方式唤醒大家,但年轻人只关心什么时候能去大陆旅游,什么时候凤梨能多卖一点。 这种现实不是他不懂,而是他接受不了。他以为理念可以唤醒民众,但最终被民众的冷漠击败。 外部环境更让他绝望。绿营趁火打劫,把郑丽文塑造成“洪秀柱2.0”,挑动蓝营内部对立。 赵少康也来搅局,说什么“介选说”,逼郑丽文表态“压制亲陆势力”。这一切加在一起,让他明白,他的位置已经不只是被边缘,而是被彻底排除在外。 他曾经寄望的孙文学校,如今也失去了中心。他退出后,这个以理念为旗帜的组织失去了灵魂。 他的支持者,不是去新党,就是沉默。统派,在台湾政坛的空间,已经几乎归零。 这次选举最大的残酷,不是张亚中输了,而是他终于明白自己从来没有赢过。他从来没有被这个政党真正接纳过,只是被容忍,被利用,被冷落。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国民党的“灵魂守望者”,但现在他知道,他只是一个遗世独立的旁观者。 投票率只有39.46%,这不是冷漠,这是沉默的抗议。超过六成的党员用不投票的方式,表达对这场权力游戏的无感。 张亚中看得比谁都清楚,但他知道,这种沉默不会成为理念的胜利,只会让功利主义走得更远。 张亚中最后的那篇长文,没有一句责怪,却句句是诀别。他说自己“郁郁不得志三十年”,这不是抱怨,是告别。 他说“隐形的翅膀终究没能飞过大海”,这不是哀怨,是认命。他不是输给郑丽文,而是输给整个时代。 他退出了,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理想主义者。 他退出了,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太清醒的人,在浑水中活不下去。 他退出了,不是因为他失败了,而是因为他终于看清了,自己从来没有被需要过。 这一场败选,不只是一次数字上的瓦解,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三十年信仰的坍塌。 他不是离开政坛,他是被这个政坛彻底抛弃了。而这一次,他连愤怒都没有。只有沉默,只有绝望,只有一个人的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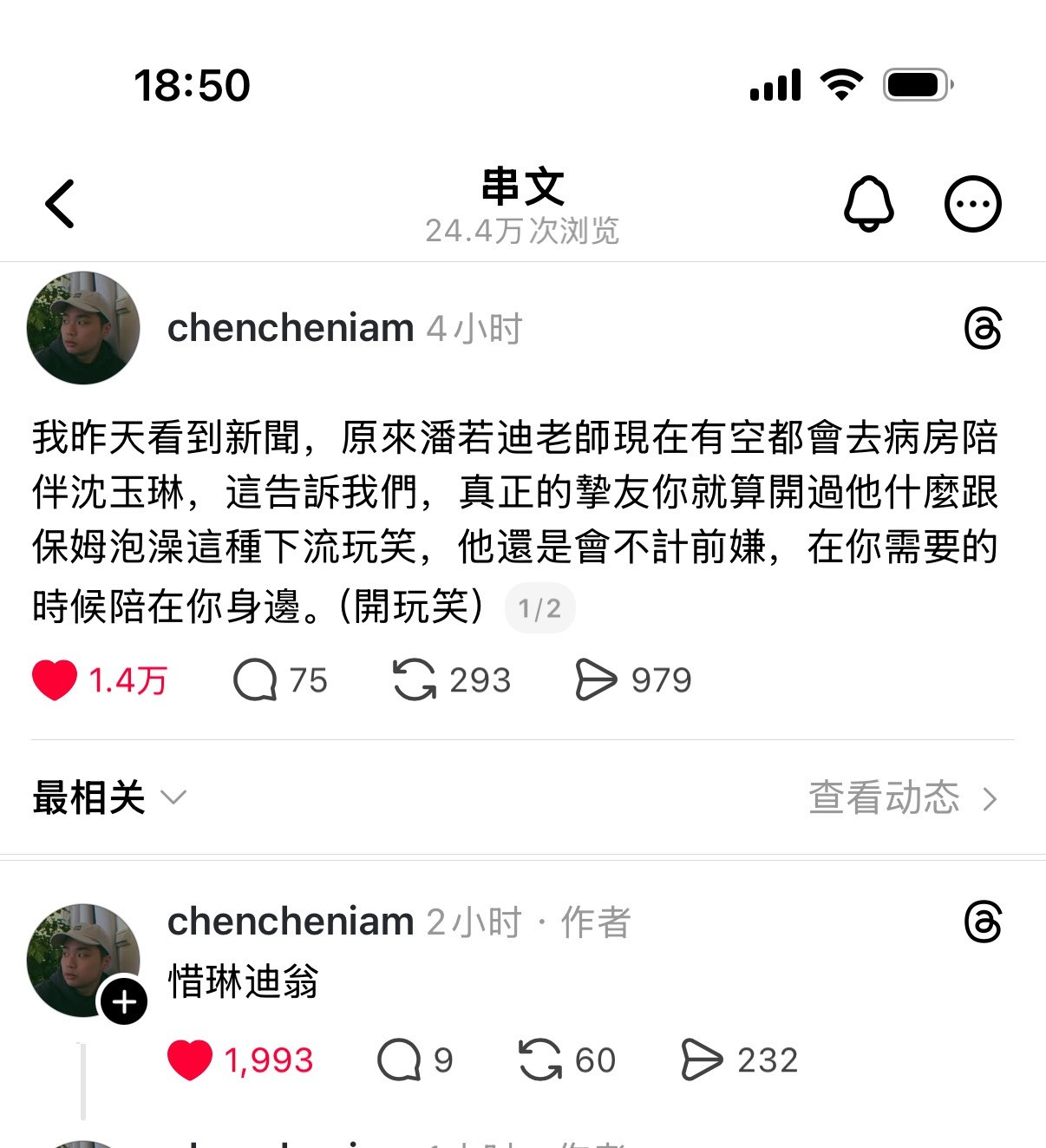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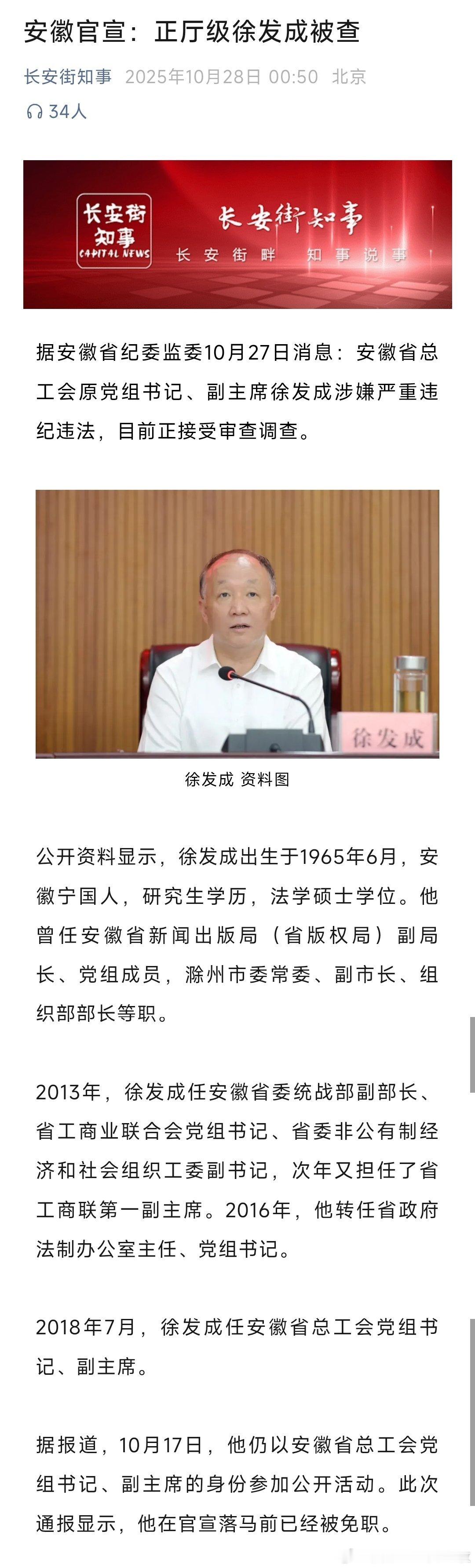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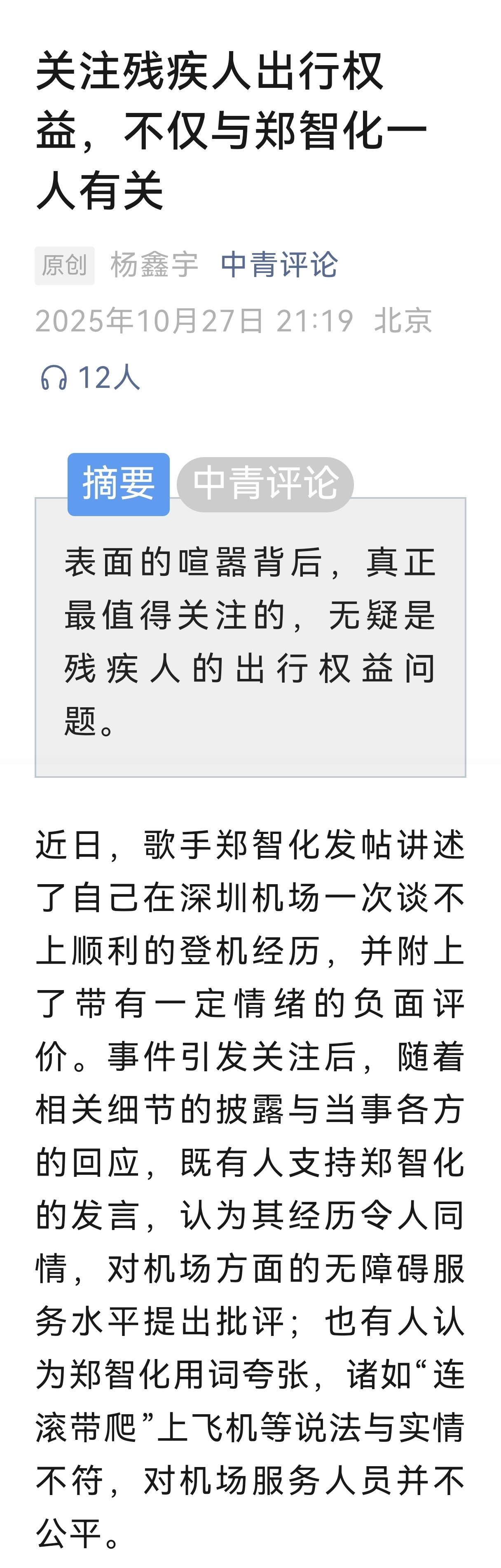


用户11xxx18
有鲁迅先生的文风和骨气,也是中华民族脊梁的一份子!
江山如此多娇
空想不等于理想,实现不了的想法就是空想。理想是不光有想法,还要有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措施。
PANDA
亚中不要灰心!更加旗帜鲜明促进统一!已经到了谷底每一条路都是上坡!
用户11xxx18
有鲁迅先生的文风和骨气,也是中华民族脊梁的一份子!
嘿呦喂
张亚中适合理论研究和讲学!
一聊永谊
加入共产党吧
飞翔
张亚中不要自以为是!不团结统派独来独往,孤家寡人有鬼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