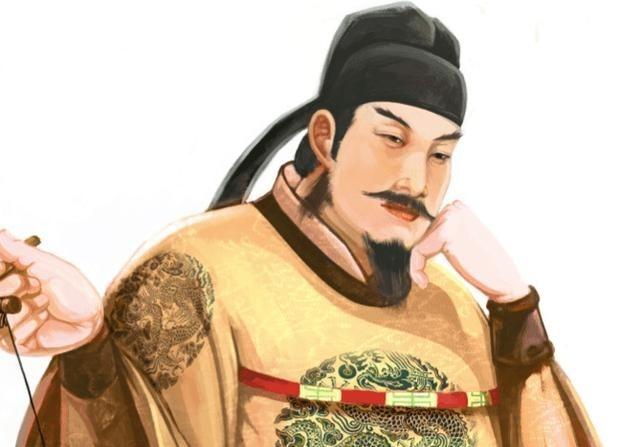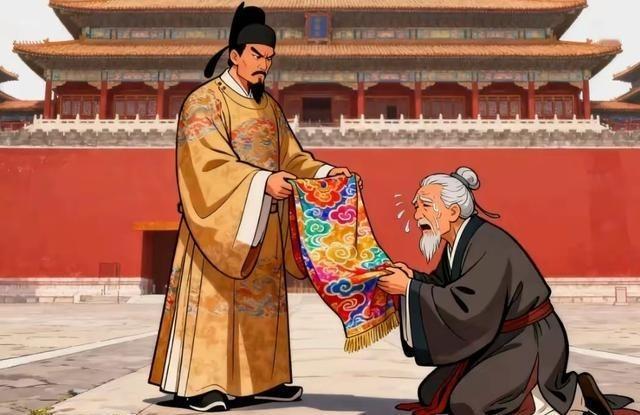毛主席评唐太宗李世民父子;“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如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远处有人把李世民叫作“天可汗”,近处也有老学者给他打光。 法国的勒内格鲁塞说他改写了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分量不轻。毛主席评他“稍逊风骚”,意思只在文采,气魄不减。少年时的李世民,聪睿、果断、不拘小节,做事干脆,跟人下棋不拖泥。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响动一声闷雷,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血溅宫墙,旋即册立皇太子,后登基把朝局拎稳,贞观之治从这张桌面铺开。 这位皇帝喜欢把日子排得满满当当:鸡鸣入朝,退朝就拉大臣掏心窝子,专谈政事;日影西斜,又把学士请进来,高谈经史,间插玄言,常常熬到深更半夜。 李百药在《封建论》里夸他“四道”,毛主席读到这里,干脆点一句“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与民休息,不搞虚张声势;勤于政事,戒玩物丧志;善纳群言,不做独断官;博学于文,不肯自我设限。四条拿在手里,像四根钉子,把朝廷的作风钉在墙上。 与民休息不是嘴上说。新朝初定,劝他耀兵振武的声音不少,他偏偏选择收刀入鞘,去奢守俭,把国本先养起来。 外面不胡乱耀武,布德施惠,免得“妄劳中国”。 等到内外都安稳,远人反而自己来投,盛唐气象抬头。勤政这一条也不含糊,奏章里有中肯之言,亲手贴在卧室墙上,抬头就能看见。升仙楼有人请看球,他要了球,当众一把火,火苗蹿起,满座噤声:帝王起个头,天下就跟着跑,耽误正事,划不来。 纳谏这道门一开,风就透了进来。 贞观元年,元律师案判死,司法官孙伏伽顶着压力直言不当,李世民不但不恼,还赏下兰陵公主园,价重百万。 重赏不是为花园,是在给朝堂立规矩:只要讲理,就不怕开口。 由此留下许多硬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人为镜明得失,以史为镜知兴替。后人把当时的对话掐出来,编成《贞观政要》,做天下储君的床头书。 书卷气把帝王气熨得服帖。 天策府开文学馆,广延十八学士:虞世南、褚亮擅文辞,孔颖达、陆德明通经史,房玄龄、杜如晦懂治道。馆中值宿,军政一歇即入阁讨论;即位后又设弘文馆,分班值夜,讲论不绝,常至“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诗句也有脊梁:“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读书不是摆样子,是真要从典籍里摸出风化与政理的门槛。 说到打仗,他的手法干净。自己总结“以弱当强、以强当弱”。 弱时佯攻牵制诸路,强处就把兵力掷到一点上,以五六倍之众,四面裹住,一口吞下。 霍邑之战,晋阳起兵西进遇隋军顽抗,秋雨连绵、军粮见底,主帅有退意,他劝止,强调先取咸阳以定人心,随后身先士卒,打通关中门户。 对陇右薛举,选择坚壁不出,相持六十余日,等对方粮尽气衰,一击而破;期间因病交由刘文静主事曾失利,再起炉灶仍按原方针,稳扎稳打。 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一一处置,干净利落。 对战争的态度不飘:兵甲是凶器,土地再宽,好战也要民凋;边境再安,忘战也要民殆。不可全除,也不可常用,分寸要拿稳。这套分寸,后来得到了重量级点名。 毛主席批注《智囊》时拎出这条要领,又下结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把李世民与曹操一起称“会打仗”。 集中优势、全歼速决,不只是战场的算盘,也是士气的杠杆:敌军被歼一团就少一团,我军补足枪口与兵员,气势腾起,增援来不及落地便化作空响。 朝廷另一头,是立储这道坎。 嫡长子李承乾从小聪敏,得父皇器重,常在侧听断庶政;年岁一长,迷上声色,不理政务,还染足疾“不良于行”,威仪受损。 魏王李泰心思不小,晋王李治性情仁孝而弱。李世民瞧中李恪,称其“英果类我”,贞观十二年也就是六三八年赴安州就任前,专门嘱一句“宜自励志,以勖日新”,还盘算着让其外藩成屏。 朝中阻力不小,长孙无忌等极力反对改立。 几番权衡,最终立李治为太子,后为唐高宗。对这桩选择,毛主席在读《新唐书李恪传》时写下那句重话:“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把账摊开看,也能看出另一层心事。 玄武门的阴影还在墙上,兄弟相残的血痕难以洗净。立李治,或能保障同母三子相安,也便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搭出彼此牵制的辅政班子,免得一派坐大。成效并非空话。 李治承贞观遗风,重用名臣,重视科举,亲自策试举人,选入弘文馆待诏;法制上修成《唐律疏议》,成为现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法典;经济稳步,人口统计到三百八十万户;军功方面,大破西突厥,稳定西域,远征高句丽,朝鲜半岛第一次纳入版图,唐代疆域在他手上撑到最大。 诗歌能照见脾气。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里有“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刀光翻在寒风里。 毛主席《五律张冠道中》写“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两句隔着朝代握手,冷气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