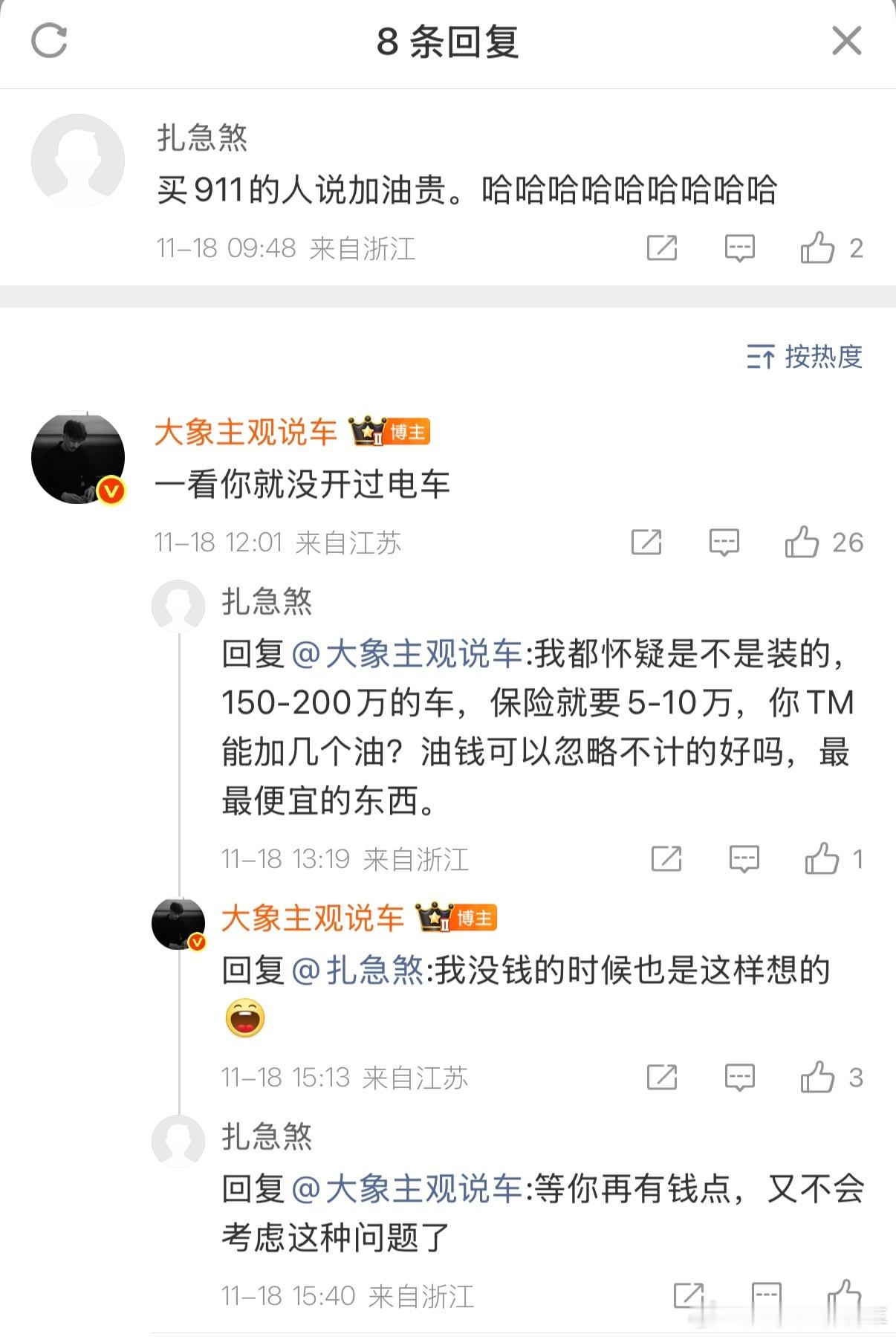原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上将。在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中,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张连忠被提拔为海军副司令员。1987年,张连忠接替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萧劲光、叶飞、刘华清之后海军第四任司令员。 张连忠这个人,远远看着是那种笑眯眯的老海军,真坐到饭桌边上,性子一点不软。 南沙方向下部队,路过武汉一所海军学院,后勤一听说他要来,人先紧了半截。 大家心里有数,这位最看不顺眼的,就是借“接待”搞排场那点事。 接风那天,一桌菜上来,青菜、豆腐、炖肉,样样像从招待标准里量出来的,他夹菜不多话,吃得挺实在。过了一会儿,一条肥得发亮的大草鱼被端了上来,盘子刚落桌,他脸就沉下去:“这种规格,也算普通接待?”负责的干部赶紧过去解释,说是学院自己池塘里养的,没动公家一分钱。 话说得很溜,意思就是占点“自家便宜”不算违规。 他盯着那条鱼,筷子停了停,没有把桌子掀了,这顿饭就这么压着火吃完。 第二天,一帮人觉得头一天这套说辞挺灵,又照搬一遍。 菜上到一半,一只甲鱼躺在盘子里推出来,汤还在冒泡。张连忠抬眼一看,筷子都没抬:“端回去。”那句“池塘里养的”又被搬出来,他这回一点缝都不留:“谁养的不重要,不合规就别端上来。”随行干部在旁边打圆场,说菜都烧好了,不吃浪费。 他把椅子往后一挪:“心疼你们吃,别算在我头上。”甲鱼只好灰溜溜退回厨房,这桌人算是被他当场按在规矩里。 这事很快在海军系统传开。 嘴上当笑话讲,心里都明白,他拒绝的不是一只甲鱼,而是那条大家习惯往下压一压的“标准线”。 战争年代靠冲锋,和平年代,很多人就是在一桌饭、一趟车上慢慢滑下去的。 能在嘴边那一口上说“不”,遇到更大的诱惑,心里才有硬东西。 时间往前拨到一九八五年,百万大裁军铺开,铁道兵、工程兵整建制撤下去,大军区机关降格,很多军长、师长的位置都在往回收。 海军一边瘦身,一边琢磨怎么把有限的员额和经费往“刀刃上”挪。 旅顺基地那张任命表上,张连忠的名字被提了出来,从基地司令员挪到海军副司令员,正好站在裁军和转型交叉的槛上。 同一时期,海军还在走另一条“硬路子”,一九七五年,刘华清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时,就在《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里直说,海军“陆地味太重”,不研究海洋,不抓技术,这样搞下去“难以想象”。 一九八二年八月,他从副总参谋长调任海军司令员,上任不久就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撂下句实话:是不是现代化海军,就看有没有现代化武器装备,当司令的人不抓装备,别的都白搭。 他动手的方式很简单:先把原来七零八落的几个装备研究所、研究室拧成一个军级“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专门替舰艇、导弹、雷达这些东西算细账;再对现役舰艇、飞机做一遍“家底盘点”。 从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起,到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止,海军分五次集中退掉老旧舰艇。 码头一下子空出来不少,修理费省下一大块,人也腾出来,成批送进海军院校,为后面接新舰、新机当技术骨干。 装备减掉了,往哪儿加,得有谱。 一九八四年,海军开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刘华清把话摊开:一九九零年前先打基础,眼前这批算“第一代”,能改就改,能补就补,同时要预研“第二代”,潜艇、导弹舰艇、海上特种飞机得先顶上。 一九八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判断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军队建设要从临战状态转到长期现代化,他干脆把原来的“七五”“八五”“九五”三个五年计划捆在一起,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用大约十五年,让海军武器装备向世界先进水平跨一截。 一九八六年年底,海军三份规划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定稿,一九八七年二月报到军委。 纸上写得很明白:打算用十五到二十年时间,做航空母舰和战略导弹核潜艇的预研,为二十一世纪的海军先把土夯好。 后来新型舰艇、飞机一批批下水、入列,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艘航母列装,往回看那几页纸,就知道那时候这步棋走得不早不行。 同一年,刘华清调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海军司令员的位置轮到张连忠。 他前面有萧劲光、叶飞、刘华清三位司令,各有各的脾气和路数,轮到他接手时,方向基本定了:从“近岸防御”往“近海防御”挪,从“数量建军”往“质量建军”扭。 他得接住这条线,同时又得把“甲鱼那张脸”带进机关和部队,让制度不是写在纸上,而是落到人手上、嘴上。 张连忠在甲鱼面前板起的那张脸,韩怀智在授衔名单里“低”出来的那半档军衔,刘华清提前十几年来回打磨的那几份装备规划,挤在同一个年代里,看上去各走各的路,细细一拼,都是一股劲儿:有人替海军把十五年以外的路先画出来,有人在三场大战里活到最后,还有人在一桌饭上也愿意说“不”。 很多年以后,新舰一艘艘靠进军港,老舰散成废钢,故事在部队里接着讲,有人记得那只被端回去的甲鱼,有人记得一九八五年的百万大裁军,也有人记得一九八八年授衔时肩上少挂的那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