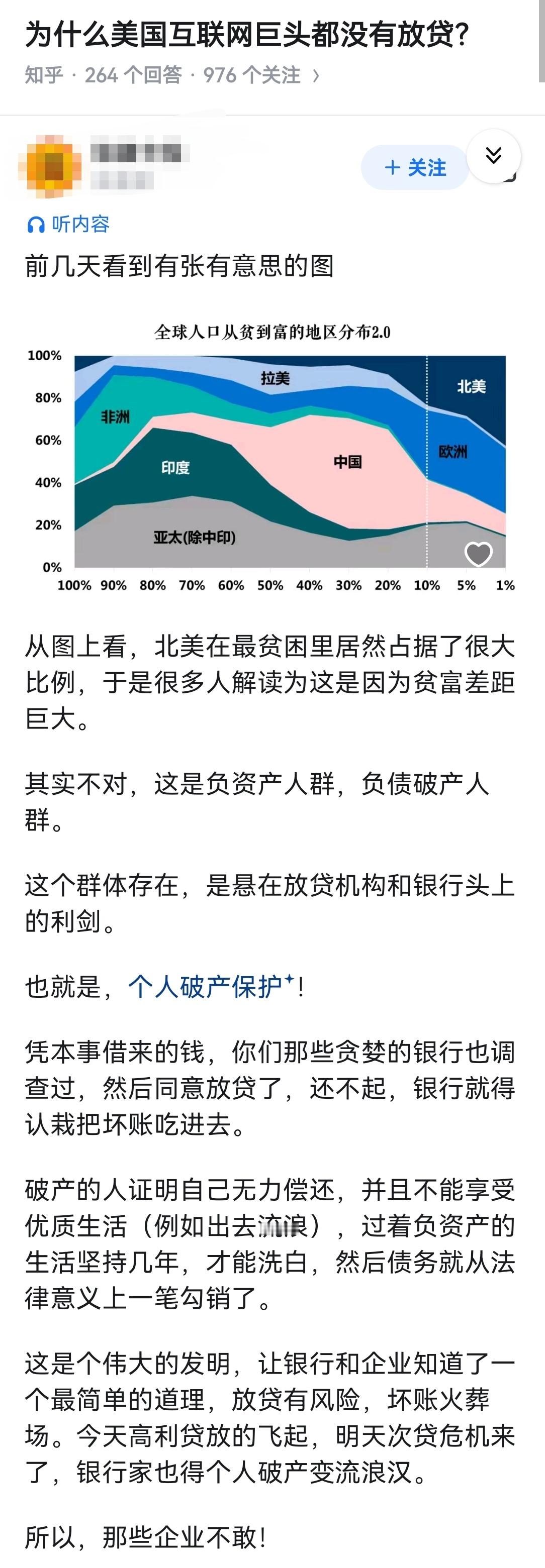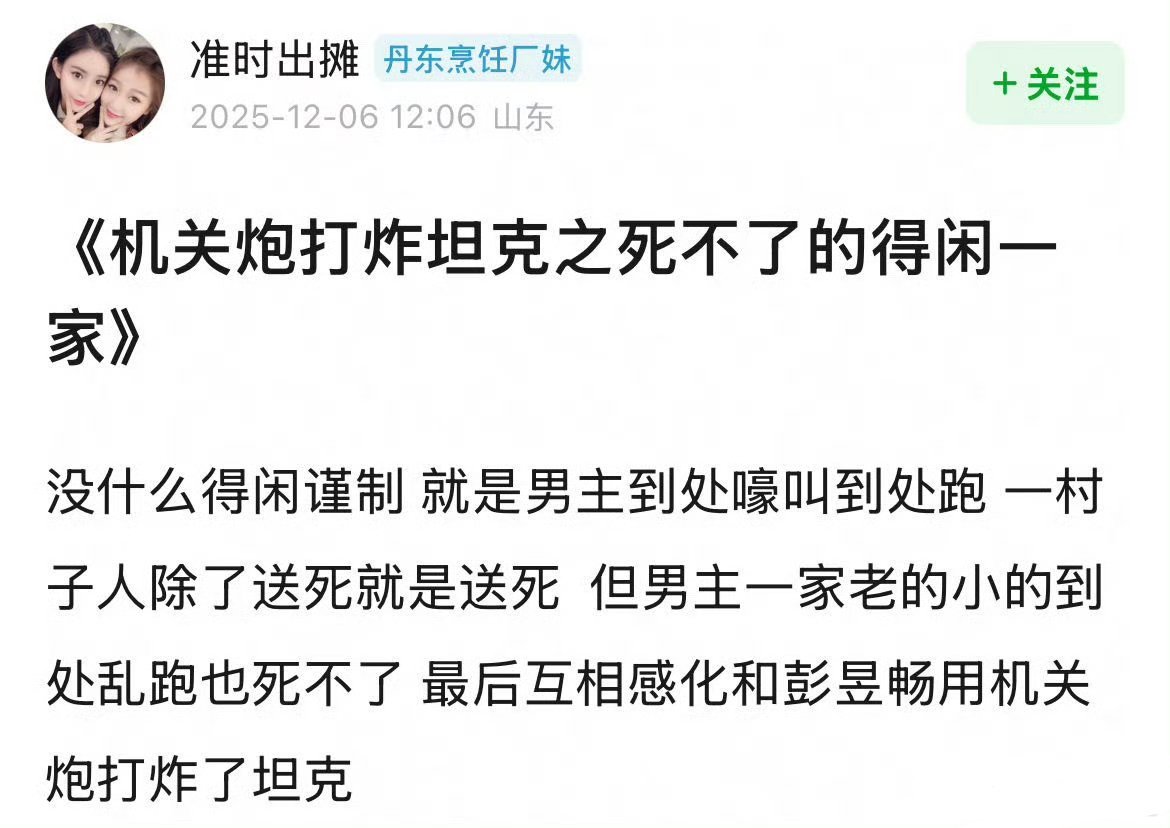冬夜里的暖光 1977年皖北的冬夜,北风像带刃的鞭子,抽得窗棂呜呜作响。我裹着单薄的被褥缩在知青点大通铺角落,借着月光翻看油印课本,油墨香混着煤油味,是我与城市仅存的联结。 突然被角一凉,一个温热的身子钻了进来。我浑身汗毛倒竖,借着微弱月光,看清是队长的女儿陈红梅。她头发上的皂角香混着泥土气息,紧紧贴着我取暖,声音闷闷的:“我冷,爹打呼噜吵。” 那个年代,孤男寡女同床共枕足以毁人名声。我急得浑身冒汗,低声驱赶,她却像块暖石赖着不动。此后半月,她每晚准时来“蹭暖”,从最初的惊恐愤怒,到后来竟成了习惯——没有言语,只是在寒夜里互相依偎,听着彼此的心跳声入眠。 白天她会偷偷塞给我烤红薯、煮鸡蛋,那些在乡下金贵的吃食,成了我粗粝生活里的甜。一次我淋雨发烧,口粮又被会计克扣,是她端来滚烫的姜汤和炒玉米面,说是从家里悄悄拿的;我砍柴崴了脚,她半拖半背把我送回知青点,捣碎草药细心敷上,眼眶通红地骂我“不要命”。 变故发生在河边。村里的二流子陈二赖调戏红梅,我抄起木棍就冲了上去。两人扭打在地,我脸上挂彩,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村长想偏袒亲戚,老队长却拎着旱烟枪挺身而出,打断陈二赖的腿,当着全村人说:“小陈是好娃。” 年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陷入狂喜与挣扎。这是回城的唯一机会,可看着红梅清澈的眼睛,我想起那些冬夜的温暖、病榻前的照料、危难时的守护。考试那天,她站在村口目送我,寒风中单薄的身影和含泪的眼眸,成了我心头最沉的牵挂。 拿到上海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老队长摆了全村最丰盛的宴席。酒过三巡,他红着眼眶求我:“把红梅带走吧,哪怕让她当个保姆。”那一刻,我突然清醒——我不能丢下这个用温暖照亮我苦难岁月的姑娘。 “我娶她。”我举杯,“让她名正言顺跟我回上海。” 回城后,父母的反对、邻居的指点让日子举步维艰。我们租住在几平米的亭子间,红梅白天洗碗做工,晚上学普通话、做家务,把小屋打理得温馨整洁。她像田埂上的野草,在陌生的城市里顽强扎根,用勤劳和善良慢慢融化了父母的偏见。 如今几十年过去,我们回到陈家屯安度晚年。每当冬夜围炉,红梅还会问我:“后悔娶我这个农村媳妇吗?”我握紧她布满老茧的手,望着窗外的月光,仿佛又看到那个钻我被窝的姑娘。 “不后悔。”我说,“你不是钻进了我的被窝,是钻进了我的命里。” 那年寒冬里的一点暖光,终究照亮了我们一生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