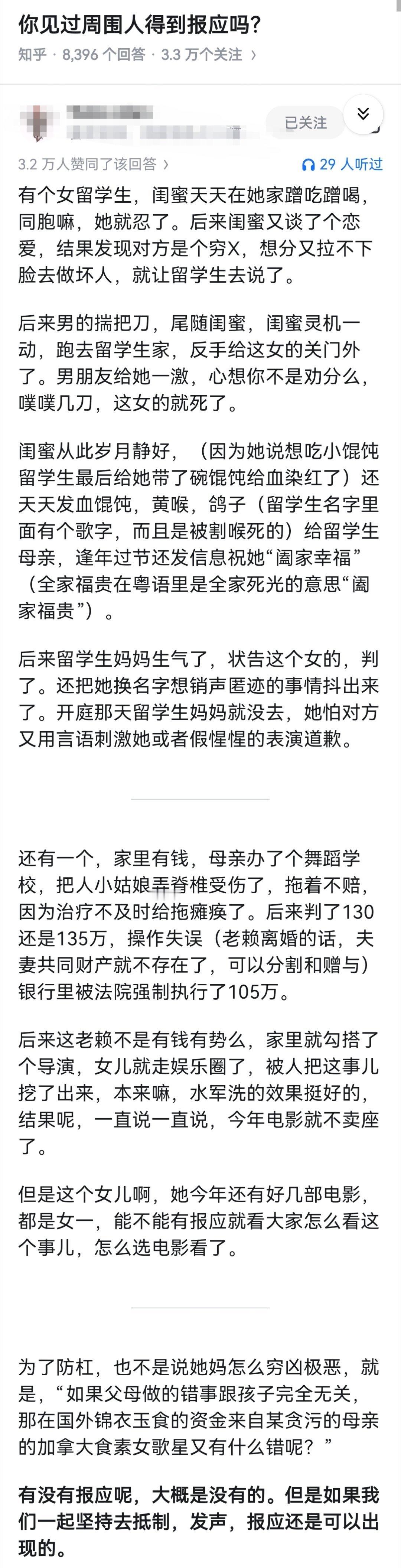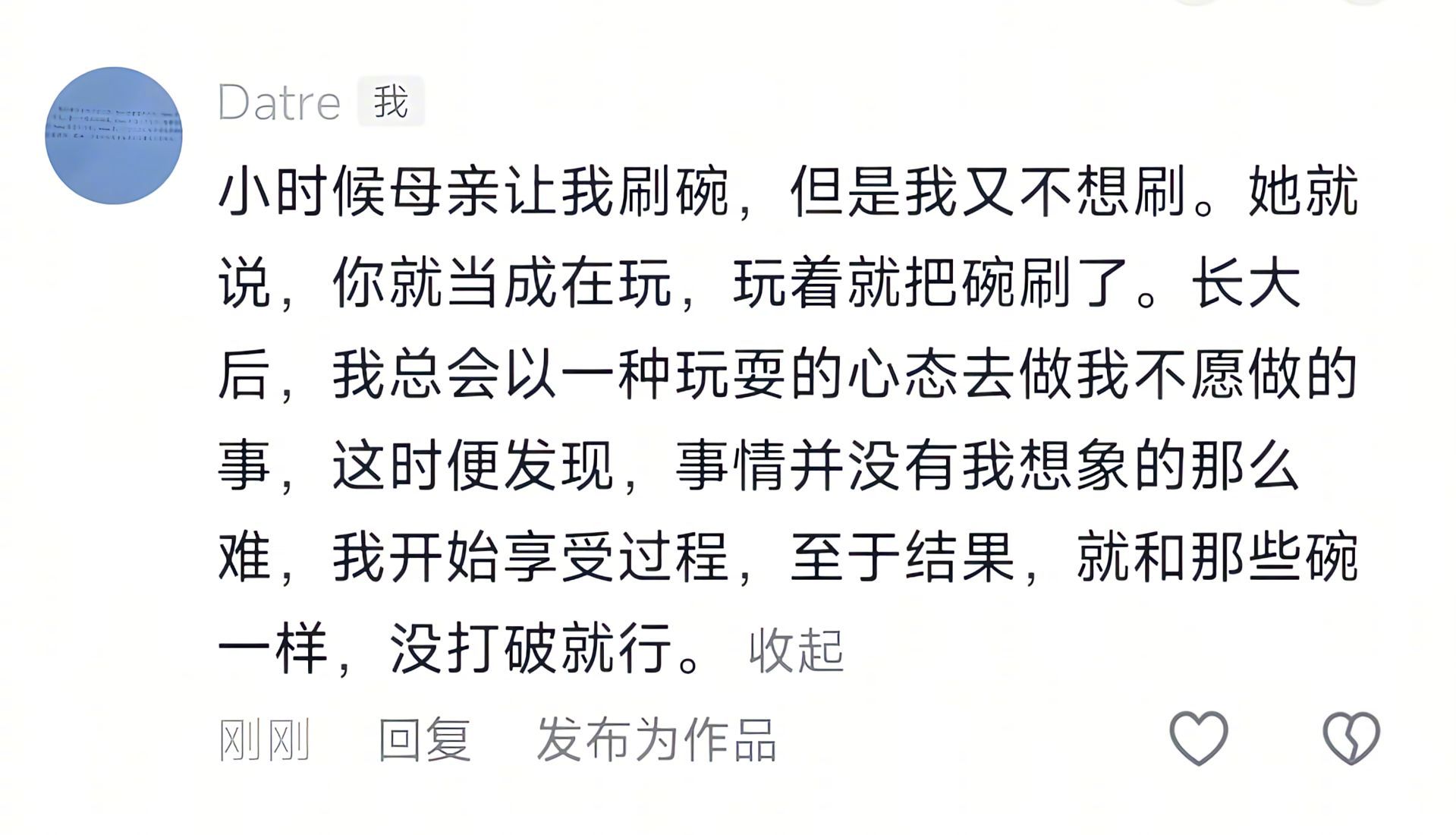令人大彻大悟的话: “好好活着吧,人死了就啥也没有了。只要你死了,不出一周,与你相关的物品不值钱的被扔掉值钱的被卖掉。不出一个月,你就将被销户,你的微信,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都会被删掉,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你这个人。不出百天,就几乎没有人想起你了,同学、亲戚、朋友饭桌上的谈资也没了。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祭日,你的家人会“欢聚一堂”为你祭拜,但绝对不会有人为你掉一滴眼泪。三年以后,你将永远消失,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你曾经来过的痕迹。” 父亲去世第七天,老周开始清理衣柜。最上层是那件灰毛衣,母亲生前织的,袖口已经磨出毛边。 父亲最后三年常穿它,坐在阳台躺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老周把毛衣拿出来时,还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父亲戒烟十年了,但气味像渗进了毛线里。 楼下传来收废品的三轮车铃铛声。老周把毛衣叠好,放进要捐的纸箱。动作很轻,像怕吵醒什么。 抽屉里有块老式手表,表带断了,表面有划痕。老周记得这是父亲五十岁生日时自己送的,当时花了一个月工资。父亲嘴上说浪费,却戴了十几年。现在秒针停在某个时刻,永远不动了。 手机忽然震动。是堂哥:“周六家庭聚会,你能来吗?”紧接着又一条:“正好说说大伯遗产的事。” 老周没回复。他把手表放进另一个箱子。这箱是要扔的。金属表壳落在箱底,发出沉闷的响声。 阳台上的花该浇水了。父亲养的三盆茉莉,有一盆叶子已经开始发黄。 微信通讯录里,父亲的头像还在。点进去,最后一条消息是半年前:“晚上回来吃饭吗?”他当时在加班,回了个“不了”。现在那个对话窗口再也不会亮起红点。 他继续整理书桌。抽屉最深处有个铁盒,打开是些零碎:褪色的老照片、几枚不同年代的硬币、一张字迹模糊的奖状,“周建国同志,先进工作者,1987年”。 老周拿起照片。年轻的父亲抱着婴儿时的他,对着镜头笑得很僵,但眼睛亮亮的。那时父亲头发还很密,衬衫领子挺括。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儿子百天”。 封好三个箱子:捐的,扔的,留的。留的最少,只有那个铁盒和一本相册。 手机又震动。这次是老同学:“听说你爸的事了,节哀。下个月同学会你来吗?好久没聚了。” 老周看了看日历。下个月18号,是父亲生日。如果父亲还在,他应该会买个蛋糕,虽然父亲总说别浪费。 傍晚,收废品的来搬箱子。房间突然空了许多。衣柜大敞着,里面只剩下几个衣架,孤零零地挂着。 回屋时,他看见墙上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那是他自己的影子,独自一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移动。 他关上衣柜门。咔哒一声,很轻,但在这个过于安静的傍晚,听起来像某个句号被最后画上。 孔子:“未知生,焉知死?” 死亡后的遗忘与消逝是必然,但正因如此,“生”的每一刻才显得珍贵。 塞缪尔·贝克特:“我们出生时就已足够老了,但我们仍有时间去死。” 真正的存在感不是建立在死后被铭记的长度上,而是在活着时感受的深度与广度上。 石黑一雄:“记忆是我们感知时间的唯一方式,而当记忆消失,时间本身也就停止了。” 好好活着,就是在创造这些无可替代的、只属于你自己的记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