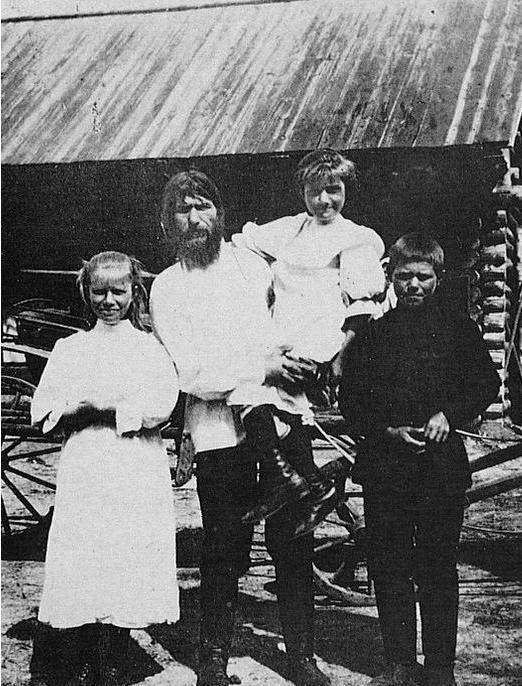苏联在战后为了能提高人均吃肉量,就大力发展鱼肉鱼罐头这些。因为猪肉牛羊肉这些产量上不来,而苏联地大物博从河流到湖泊再到大海都能捕获很多鱼,于是就从上到下大力推广鱼罐头这些。 1945年,苏联刚从战争废墟中爬出来,粮食紧张不说,肉类更是稀缺得离谱,猪牛羊不是你想养就能养,战争把畜牧业几乎摧毁了个底朝天,怎么办?领导层一拍脑门:我们没有肉,但我们有鱼啊! 全国从黑海到太平洋,河湖海洋密布,水产资源丰得流油,于是1946年,苏联专门成立了渔业部,还找来了个行家,伊什科夫,他不是空降干部,而是真·伏尔加河渔民出身,懂行也敢干。 他一上任就搞大动作,不是修鱼塘,而是直接上远洋捕捞,两万多艘渔船开出去,全球撒网;罐头厂一排排建起来,冷冻设备、自动化线统统安排上。 鱼从海里捞上来,几小时就能装罐进仓库,速度快得像流水线出兵,要让全国老百姓接受从“大肉”转向“鱼肉”,光生产不行,还得营销。 苏联的办法很简单粗暴,那就是规定每周有一天必须吃鱼,工厂食堂、学校食堂、政府机关,全都统一执行。 苏联和美国在二战后都面临食品供应的问题,但由于制度、资源禀赋和战略目标不同,两国在战后食品供应的策略上呈现出明显分化。 苏联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路线,国家定指标、定任务、定供应,从中央到地方一条龙操作。 食品不是市场商品,而是“战略资源”,像鱼罐头这种东西,能不能吃,不取决于市场喜好,而是国家安排。 而美国完全不同,靠的是市场机制,农业是市场主导,但政府通过补贴、价格支持等手段稳定生产,战后美国农业机械化、化肥使用爆发式增长,农民种多种少自己说了算,政府负责兜底。 苏联靠“统”,美国靠“养”,一个是“我告诉你吃什么”,一个是“你想吃什么我帮你种”。 由于苏联畜牧业崩溃,苏联在战后用“鱼肉”替代“猪牛羊”,搞了个全国性蛋白质替代计划,鱼罐头、鱼日制度、远洋捕捞成了国家战略,不是因为想吃鱼,是没得选。 美国有技术、有资本、有土地,直接走的是“增产肉类”的路线,大规模养殖业兴起,玉米、大豆种植配套发展,用饲料堆出一头头肉牛和猪。冷藏技术也飞速发展,肉类消费直接起飞。 美国把食品当成产业链优化,农业和工业联动,食品加工、运输、冷链、超市系统全面升级,凯洛格早餐谷物、斯威夫特冷冻肉类、雀巢罐头等企业迅速崛起,商业推动消费升级。 到了70年代,苏联终于迎来了“幸福时光”。不是因为农业丰收,而是靠着油价飞涨,出口原油换来的大把外汇。 这一波“石油红利”,让苏联终于可以不靠鱼罐头凑合了,他们开始大规模进口肉类:从阿根廷拉牛排,从澳大利亚进羊肉,从加拿大买猪肉,商店货架上,鱼罐头不再是唯一选择,真正的“肉”终于回来了。 苏联和美国的战后食品策略,某种意义上,是两种国家路线的缩影。 苏联用“鱼罐头”撑起了战后几十年的餐桌,是计划经济下的应急智慧,却也暴露出系统的僵硬和脆弱;而美国则用农业科技和市场机制,把“餐桌”变成了产业链,最终成为全球粮食出口强国。 一个是“资源型国家的无奈选择”,一个是“工业农业结合的成功案例”。两种路径,没有绝对的对错,但谁走得更远,历史已经给出答案。 从战后废墟到远洋渔船,从国家动员到市场调节,鱼罐头不是苏联的“奇迹”,而是它不得不走的现实之路。它既是资源战略的产物,也是制度逻辑的体现。 在苏联那种计划经济体系下,鱼罐头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一场可控的、从上到下的资源配置实验,它解决了战后蛋白质缺口,也展示了“有资源就能顶上”的国家能力。 但这套模式也暴露出一个问题:一旦失去外部支撑,比如油价崩盘,整个体系就显得脆弱无比,苏联靠鱼罐头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却没能为自己建立一个真正多元、可持续的食品供应系统。 苏联的鱼罐头,曾是救命稻草,也是战略工具,但它从未成为真正的答案,今天回头看,这场“全民吃鱼”的国家实验,留给后人的是一道关于发展路径的深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