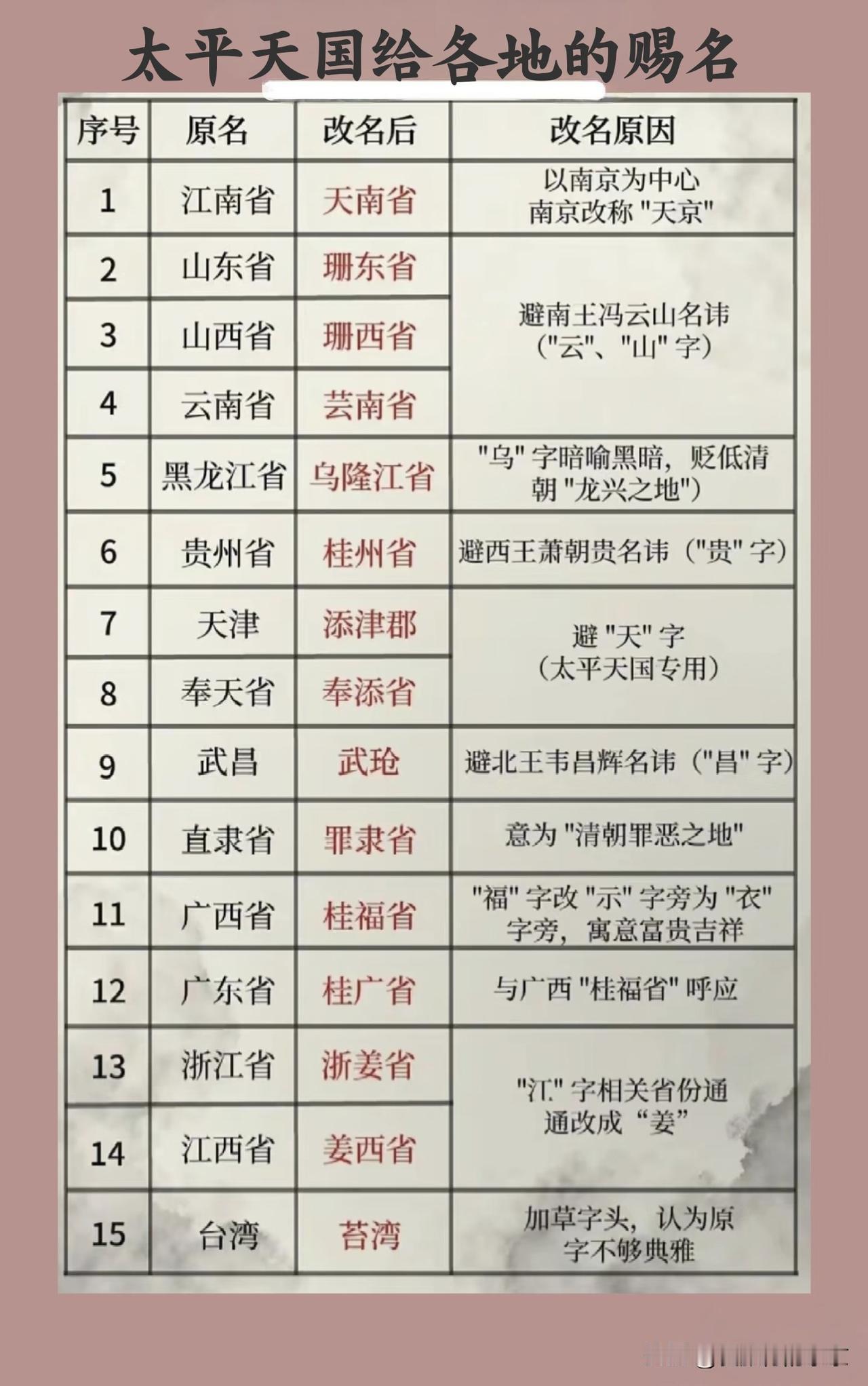她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没有这个女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959年的韶山冲,初夏的风吹过松林,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独自站在一座土坟前。他是被亿万人仰视的领袖,但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束带露水的松枝,神情却像极了那个曾经满山跑的“石三伢子”。他在坟前鞠了三个躬,轻声说了句只有风能听见的话:“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这句话的重量,全压在那块墓碑的主人身上——文七妹。 在这个家里,父亲毛顺生像一块坚硬冰冷的铁。他精明、勤勉,一生都在算计着怎么把家业做大,指望长子能学算盘、记账,把家里的米店生意撑起来,而母亲文七妹,则是包裹这块铁的棉花,更是那个用柔韧对抗坚硬的人。 1867年出生的文七妹,大名叫文素勤,虽然那个年代女人多半没有正式名字,但她在娘家湘乡县唐家坨却是备受疼爱的。 十三岁那年,因为文家信了风水先生的话,觉得韶山是块宝地想迁祖坟,这桩亲事便带上了几分家族利益交换的色彩。还是个孩子的她,就这样走进了陌生的毛家,成了比自己还小三岁的毛贻昌(毛顺生)的童养媳。 虽然不识字,一辈子也就是围着灶台和孩子转,但文七妹有着一般农妇少有的生活智慧。 由于前两个孩子接连夭折,那是任何一位母亲都无法承受的锥心之痛,所以1893年冬天那个男婴降生时,文七妹是欢喜中带着惊恐的。 为了保住这一脉骨血,她近乎执拗地尝试着民间所有能想到的法子:她吃“观音斋”祈福,把孩子抱回风水“更好”的娘家抚养,甚至让儿子去拜后山上的一块巨石做干娘,给他取了个贱名“石三伢子”,就盼着这孩子能像石头一样硬邦邦地活下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个唯唯诺诺的软弱妇人,恰恰相反,在这个家庭里,她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战斗。 饥荒年头,或者遇到逃荒乞讨的,家里那个精明的丈夫总是紧闭大门,生怕家底被分薄。文七妹不管这一套,她看不得人受苦,丈夫在前面看管得严,她就在后面偷偷送米、送饭。 她信佛,但这信仰不是求自家升官发财,而是落实到了一粥一饭的慈悲里,她常对孩子说,“多做善事,子孙才会有好报”,甚至调侃自己这是“损己利人”。 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学堂的午餐时间,少年毛泽东发现同学“黑皮伢子”没饭吃,就瞒着家里把自己的午饭分出一半,时间一长,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饿着肚子回家,自然瞒不过母亲的眼睛。 得知原委后,文七妹既没有责怪儿子“傻”,也没有抱怨粮食金贵,而是第二天默默在饭盒里装了两份饭。这不仅是对善良的纵容,更是一种无声的教育——由于她的这种托举,那种对底层苦难天然的共情,便在少年心中扎下了根。 如果说生活上的接济是慈悲,那么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文七妹则展现出了惊人的决断力。 当毛顺生执意要强迫长子辍学去米店当学徒时,父子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父亲要的是现世安稳的接班人,儿子要的是能够改造社会的真学问。在这个家里说话最有分量的本来是父亲,但这次,一向温顺的文七妹坚决站在了儿子这一边。 她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懂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但她懂得儿子的心。为了帮儿子争取机会,她甚至动员了娘家的亲戚轮番来劝说顽固的丈夫,硬是帮儿子要把紧锁的家门撬开了一条缝。 这扇门一开,走出去的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儿子要离家去求学,去搞那不知道能不能成的“大事”,她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舍,常常夜里睡不着觉,但临了也就是默默打包好行李,缝补好衣裳。 在那些分别的日子里,儿子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文七妹不懂他在外面的惊涛骇浪,只知道儿子是在“给穷人办事”,这便是她心里最大的慰藉。 遗憾的是,命运并没有给这位母亲足够的时间来见证儿子的成就。 1919年,文七妹患上了严重的腮腺炎。虽然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把她接到长沙治疗,哪怕革命工作再忙,他和弟弟毛泽覃也会挤出时间亲手侍奉汤药,但这还是没能留住操劳一生的母亲。 去世时,她才五十出头。更让人痛心的是,最后弥留之际,大儿子因为正忙着驱赶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没能守在床前。据说她临终前一直呼唤着儿子的乳名,直到最后一口气。 当毛泽东星夜兼程赶回韶山,看到的只剩下冰冷的灵柩。那一夜,这位从来不轻易流泪的铁骨男儿,在昏黄的油灯下守在灵前,挥笔写下了那篇字字泣血的《祭母文》。“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这不仅是儿子的评价,更是一个平凡农村妇女留在历史上最厚重的底色。 很多人都说,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伟人。其实倒不如说,是她用自己柔弱却坚韧的肩膀,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旧时代,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少年撑起了一片即使在寒冬也能感受到温暖的天空。她的名字可能不如那些风云人物响亮,但她的血液,早已流淌在这个国家重生的脉络里。 信源:红歌会网——母亲节:写给这位伟大的母亲,是她孕育了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