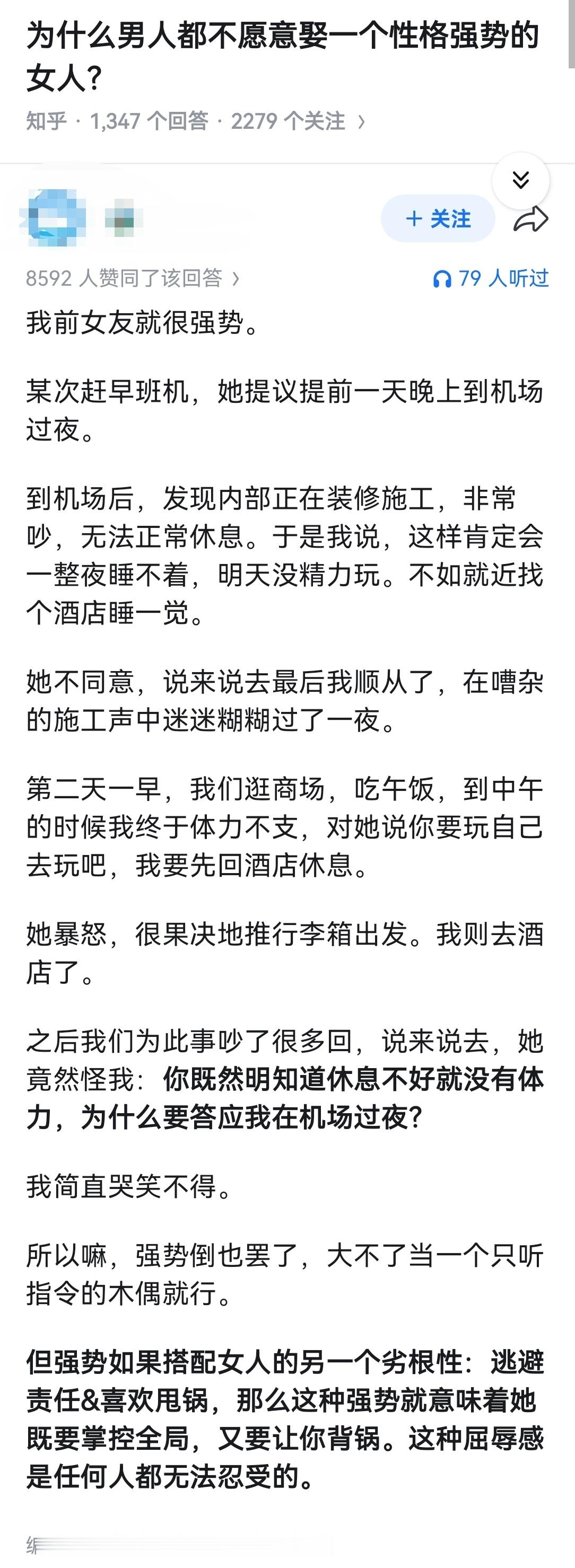[微风]张宗昌一日回家四个姨太太在打牌,女人一见张宗昌回来了,都不约而同的围在张宗昌身边献媚。 那个下午,济南张公馆的西厢房里原本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骨牌砸在红木桌面上清脆的“啪啪”声,屋里头烟雾缭绕,四个女人正处在战局的焦灼时刻,连旗袍上的盘扣松了都没人顾得上理会。 哪怕是1927年,这城里能像这样把日子过得不知今夕何夕的,大概也就只有督办府的后院了,可这一派乌烟瘴气的祥和,仅仅维持到那几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响之前,那是辆美国产的福特车,紧接着是大门口皮靴磕碰的立正声——张宗昌回来了。 这一刻简直就像是谁按下了静音键,刚才还要吃碰杠的泼辣劲儿瞬间没了,十七姨太把刚摸到手的好牌往桌上一扣,七姨太那个正准备喊话的天津嗓门硬生生憋了回去。 她们太懂这院里的生存法则了,牌桌上输赢那是闲钱,若是把那位身高一米九的“老天爷”哄不好,那是丢饭碗的大事。 当那个腰里别着家伙、穿着一身锃亮督军制服的高大男人迈进门槛时,屋里的气氛已经变了,前一秒还是乃至厮杀的赌友,下一秒这四个女人就马上变得毕恭毕敬。 最懂事的四姨太,不显山不露水地接过军帽和外衣;说话细声细语的八姨太早已备好了湿毛巾,不管不顾地往男人满是油汗的额头上招呼。 年纪最小、才十九岁的十七姨太仗着受宠,整个人恨不得贴上去,替他解风纪扣的同时,还没忘在他那满是胡茬的脸上留下个口红印。 这种活色生香的场面,若是那是放在当下的短视频里,高低得配上个“霸道军阀俏姨太”的标题,但要是真的把时光倒流回去,你会发现那一屋子的娇嗔背后,全是谋划和算盘。 张宗昌这人有个混号叫“三不知将军”,不知道兵多少,不知道钱多少,更不知道姨太太有多少,这最后一条绝不是什么风流雅趣,而是实打实的混乱。 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女人的身份比草都不如,为了方便管理,因为人实在多到记不住,张宗昌干脆给女人们发刻着号码的金牌。 不管是之前就在的苏杭名伶,还是家里硬塞来的,甚至是输了钱被卖进来的,在他眼里不过是个数字。 你看看那些留存下来的老照片,比如十九姨太卢辅义,明明穿着当时最时髦的绸缎旗袍,戴着亮闪闪的耳坠,可那眼神里别说爱意了,连点活人气儿都没有,只有被生活熬干了的苦闷。 她们拼了命地往前凑,又是递烟又是献媚,不是因为这身高马大的山东大汉有多大的人格魅力,而是为了拿到那一纸去账房领钱的“通行证”。 副官李子清手里把持着银根,今天谁哄得督办高兴了,谁就有买胭脂水粉的钱;谁若是成了角落里的冷板凳,那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吃香喝辣,这根本不是什么爱情故事,这是一群为了生存而在这座金丝笼里竭力表演的“打工人”。 在张宗昌的逻辑里,女人从来不是伴侣,而是极好用的“资源”和“面子”,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他那个极具江湖气的段子:撞破了一位姨太太和副官的私情,按照那个年月军阀的暴脾气,这怎么也得是血溅五步的下场。 可张宗昌呢?他问那副官是不是动了真心,确认之后,非但没掏枪,反而摆摆手让人去支了一笔钱,连人带钱把那姨太太送给了副官。 旁人看这是心胸宽广,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女人的廉价,在他看来,用一个玩腻了的编号女人,换一个下属对他“肝脑涂地”的死忠,换一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这买卖划算得很,比起全省一年的教育经费能被他随手输在牌桌上,这点“遣散费”对他来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他用这种粗鄙又精明的方式,维系着他在山东地界的统治,也维系着那张庞大的麻将桌不至于散架,但他忘了一点,建立在银圆和枪杆子上的关系,脆弱得就像纸糊的窗户。 这道理在1932年的济南火车站得到了印证,当刺客郑继成那三枪响过,张宗昌倒在月台上的那一刻,他那个用钱堆出来的“家”瞬间崩塌。 就在他断气后的那几个小时里,曾经在西厢房里为了争一个擦汗机会都能斗出心眼子的女人们,散得比受惊的鸟还快。 有的卷了细软跑回东北老家,有的转身就嫁了做买卖的商人,更多的则是像卢辅义那样,隐姓埋名消失在了茫茫人海的烟火巷弄里。 等到太阳落山,那座中西合璧的公馆彻底安静了下来,没人再在乎他兜里揣没揣着谁的照片,也没人再惦记晚上那一顿是去哪里应酬。 那个曾经让无数女人赔笑献媚的高大身影,最终成了民国乱世里的一抹尘埃,只剩下那些关于姨太太成群的荒唐传说,成了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信源:山东省档案馆《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档案选编》 《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卷》 《张宗昌评传》 《济南文史资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