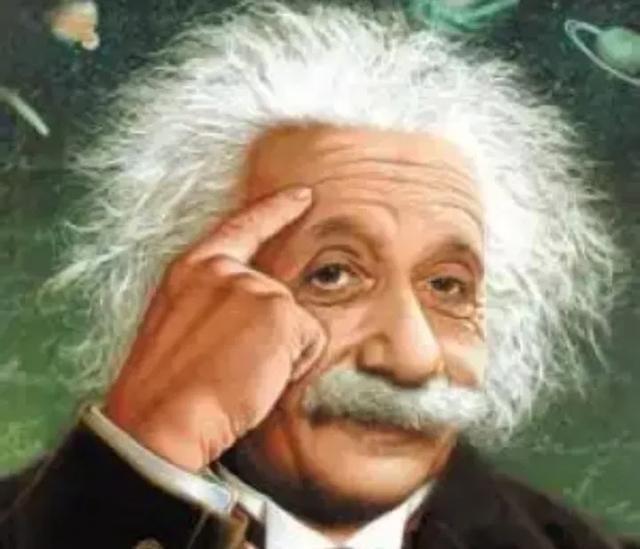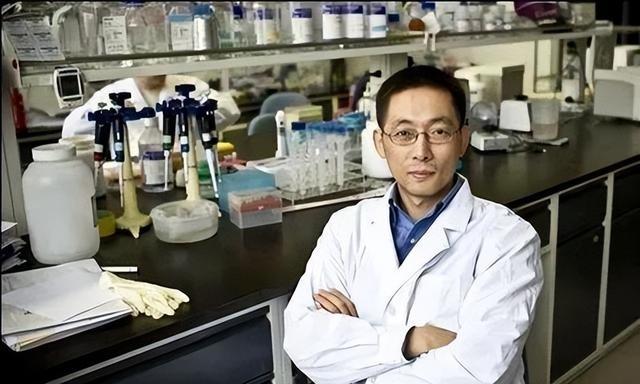中科院院士施一公有个观点,人类按现在的方式去找外星文明,结果是“一定找不到”。 这几年关于UFO、外星人的消息就没断过。前有美国开听证会,说官方藏着“非人类飞行器”,后有墨西哥这记猛料。咱们这些从小看《飞碟探索》长大的人,心里那点火苗,“噌”的一下就又燃起来了。 一方面吧,特希望他们存在,最好开着飞船来地球串个门,带来点超前科技,治个癌症、搞个清洁能源啥的,直接带咱们文明升个级。另一方面,心里又直打鼓,这事儿想想就后怕。 大物理学家霍金生前就跟咱们老百姓的爹妈一样,苦口婆心地劝:“千万别随便回答宇宙里的信号!”他那意思就是,你不知道对面是啥玩意儿,万一招来个“哥伦布”,那咱们就成了美洲土著,下场可想而知。刘慈欣在《三体》里更是把这种恐惧写绝了,整出个“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个黑漆漆的林子,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谁暴露谁就先完蛋。 叶文洁不就是对人类失望透顶,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按下了那个发射键,把三体人给招来了吗?人家三体里的和平主义者都快急死了,连发三遍“不要回答”,结果呢?还是挡不住。 这就是咱们的矛盾:又想找到他们,又怕被他们找到。可问题是,吵了这么多年,咱们为啥连根外星人的毛都没找着? 宇宙这么大,光银河系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天文学家邓李才博士说,至少有2000亿颗。2020年就有科学家估算,光是在咱们银河系,可能就存在36个地外文明。数字都这么夸张了,可宇宙还是静悄悄的,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他们都在哪儿呢? 有人猜,可能文明之间的时间窗口对不上,咱们存在的时候,他们还没诞生,或者早就灭绝了。也有人猜,地球在银河系里就是个偏远郊区,人家高等文明早就在市中心殖民了,懒得搭理咱们这“乡下亲戚”。还有更玄乎的“动物园假说”,说咱们地球就是个被圈起来的自然保护区,高等文明就在外面拿着望远镜观察,还挂个牌子“请勿投喂”。 这些猜想都挺有意思,但总觉得差点意思。直到我听了中科院院士、生物学家施一公的一个观点,才感觉脑子“嗡”一下,好像被人从一个牛角尖里给拽了出来。 施一公院士说啥了?他说,人类现在用这种方式去找外星文明,结果是“一定找不到”。 这话够绝对的吧?一个顶尖科学家,为啥敢把话说得这么死? 因为他觉得,咱们从根儿上就找错了方向。 我们现在是怎么找外星人的?咱们的探测器、射电望远镜,都在宇宙里找什么?找有水、有氧气、温度适宜的星球。说白了,咱们是在找第二个地球。咱们想象中的外星人,不管长得是像《阿凡达》里的纳美人,还是电影里那些大眼睛绿皮肤的小个子,归根结底,他们都得呼吸,得喝水,是跟咱们一样的碳基生命。 施一公直接点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们实际上不是在找生命,我们是在找和我们长得一样、行为一样,一样的大脑、一样的驱动的一个躯体。” 我们满世界找外星人,其实是在宇宙里找镜子,想照出另一个自己。我们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当成了所有生命存在的唯一标准。 施一公觉得这事儿特别不可思议。他认为,生命没有任何理由非得是碳基的。咱们人类这种碳基生命,需要恒温恒压,稍微热点冷点,气压高点低点,就活不下去,脆弱得不行。宇宙这么广阔,凭什么生命就非得是这么脆弱、这么苛刻的一种形式呢? 为什么不能是硅基生命?它们的身体由晶体构成,生活在高温高压、充满甲烷的星球上,呼吸着我们闻一下就倒的毒气。为什么不能是能量生命?一团电磁波,没有实体,在星云里穿梭,靠吸收恒星辐射为生。甚至可能存在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生命形式,生活在不同的维度里,我们从它身边走过,都互相看不见。 就像二维世界里的纸片人,永远无法理解三维世界里有个“高度”一样,我们用自己这套“碳基生物”的逻辑去找外星人,不就是在缘木求鱼吗? 这就像一个只能活在水里的鱼,它认为所有生命都必须有鳃,必须生活在水里。于是它派出潜艇,在宇宙的海洋里到处寻找别的池塘,结果找了几亿年,啥也没找到。它当然找不到,因为别的生命可能正在天上飞,在火里跳舞,或者干脆就是那片天空和那团火焰本身。 所以施一公才说“一定找不到”。因为我们的搜索范围,被人为地限制在了一个极度狭窄的框框里。我们寻找的是“人类的同类项”,甚至连稍微远一点的“异类”都没想过,更别提那些完全颠覆我们认知的东西了。 这个观点,它说的不是宇宙有多危险,而是人类的想象力有多么贫乏,我们的思维有多么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万物灵长,是宇宙的尺度。但或许,在真正的宇宙多样性面前,人类的这点认知,渺小得就像一颗尘埃。外星文明可能早就发现了我们,只是它们看我们的方式,就像我们看一块石头,一株细菌,完全无法沟通,也提不起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