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未婚,建立清华物理系,为我国培养出9位“两弹一星”元勋,却被告是“清华特务”,晚年拒绝杨振宁等学生的探望。 在中关村的大街上,钱三强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蹒跚、佝偻,他刚要上前呼唤,却见恩师像躲避瘟神一样,慌乱地摆着手,示意他赶紧走,快点离开自己。那个瞬间,这位中国原子能之父当街痛哭。 这绝非冷漠,而是一种极致的守护,叶企孙的一生,就像一个巨大的悖论。 他亲手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搭建了最坚实的地基,最终却被他所奉献的体系碾得粉碎;他把学生当成亲生骨肉,却在风烛残年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推开他们。 他的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23岁就与导师合作,测出了当时国际上最精准的普朗克常数,这个数值被物理学界沿用了整整16年。 面对西方高校的高薪厚职,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回到了那个一穷二白的祖国,对他而言,报效国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到清华,物理系条件艰苦到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他就亲自动手,带着学生修理仪器,焊接线路,经费不够,他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补贴购买材料。 他建立了一套严苛到不近人情的标准,只看水平,不问背景,就算是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也因为逃课被他毫不留情地扣掉了25分实验成绩。 他一生未婚,没有子女,却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学生身上,把他们视若己出,悄悄把自己那份牛奶口粮分给营养不良的助教,这样的事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最终,从他门下走出了79位院士,9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他构建的早已不是一个物理系,而是一个国家的科学谱系。 当战火烧来,他的守护从课堂延伸到了战场,他最珍视的学生熊大缜,一个被他视为璞玉的物理天才,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选择投笔从戎。 叶企孙心痛不已,他觉得熊搞科研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但劝说无效后,他转而用自己的方式,在后方全力支持。 他在北平、天津这些日军占领区,冒着天大的风险,利用自己的人脉和社会关系,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筹集炸药原料和通讯器材,这既是他对学生选择的最高尊重,也是一位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的抗战。 然而,1939年,熊大缜在根据地的一场“锄奸运动”中,被当成“国民党特务”错杀,未经审判,被自己人用石头活活砸死。 消息传来,叶企孙如遭雷击,从那一刻起,为学生申冤成了他后半生的一份执念,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和他15岁时因体检不合格落榜,便改名找同学代检也要考上清华时一模一样。 这份执念,也成了他晚年灾难的源头,因为曾支持过被定性为“特务”的熊大缜,在那个特殊十年里,他也成了“特务头子”。 1968年,他被捕入狱,遭受了无尽的审讯和折磨,人们逼他交出“特务组织”名单,他只回了一句:“我是科学家,我只说真话。” 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没有为了自保而攀咬任何一位同事或学生,这是在守护他们的清白,更是在守护科学的尊严和人性的底线。 1972年,他被放了出来,但人已经废了,腰弯成了九十度,双腿严重浮肿,甚至大小便失禁。他的工资被停发,只能靠着微薄的补助金,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精神恍惚,神情呆滞。 那些已经功成名就、享誉世界的学生,比如杨振宁、李政道,回国后都想探望恩师,却一次又一次被他拒绝。 不是他绝情,而是因为那时他头上的“特务嫌疑”还没有洗清,与他来往就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他宁愿独自一人被世界遗忘,也不愿自己身上的污点,玷污了这些国家栋梁的前途。 他像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在街上游荡,但偶尔见到样貌像是学生的人,会露出微笑,嘱咐几句,这位大师,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为他的孩子们撑起了一把看不见的保护伞。 1977年1月13日,79岁的叶企孙悄然离世,他的“特务嫌疑”帽子还未摘掉,追悼会上,他一生的功绩无人提及,直到十年后的1987年,他才被正式平反。 1995年,清华大学为他立了一尊铜像,但放在了一个不显眼的角落。 或许,这恰恰最符合他的精神,他一生没有发表太多论文,但他最伟大的作品,是整整一代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他甘居幕后,燃烧自己,为别人铺就通往星辰大海的道路。记住他,就是记住中国科学史上那段最沉重,也最闪光的风骨。 信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2025-07-26——“大师之师”,他培养出79位院士与10多位“两弹一星”元勋 | 叶企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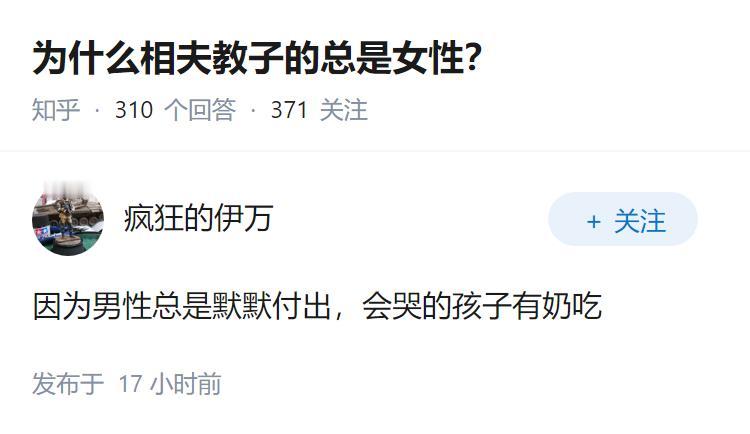


![尊界s800又在测试什么[doge]还是说又要有新款了](http://image.uczzd.cn/1419901867717439064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