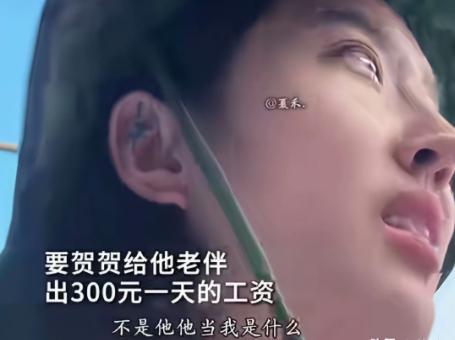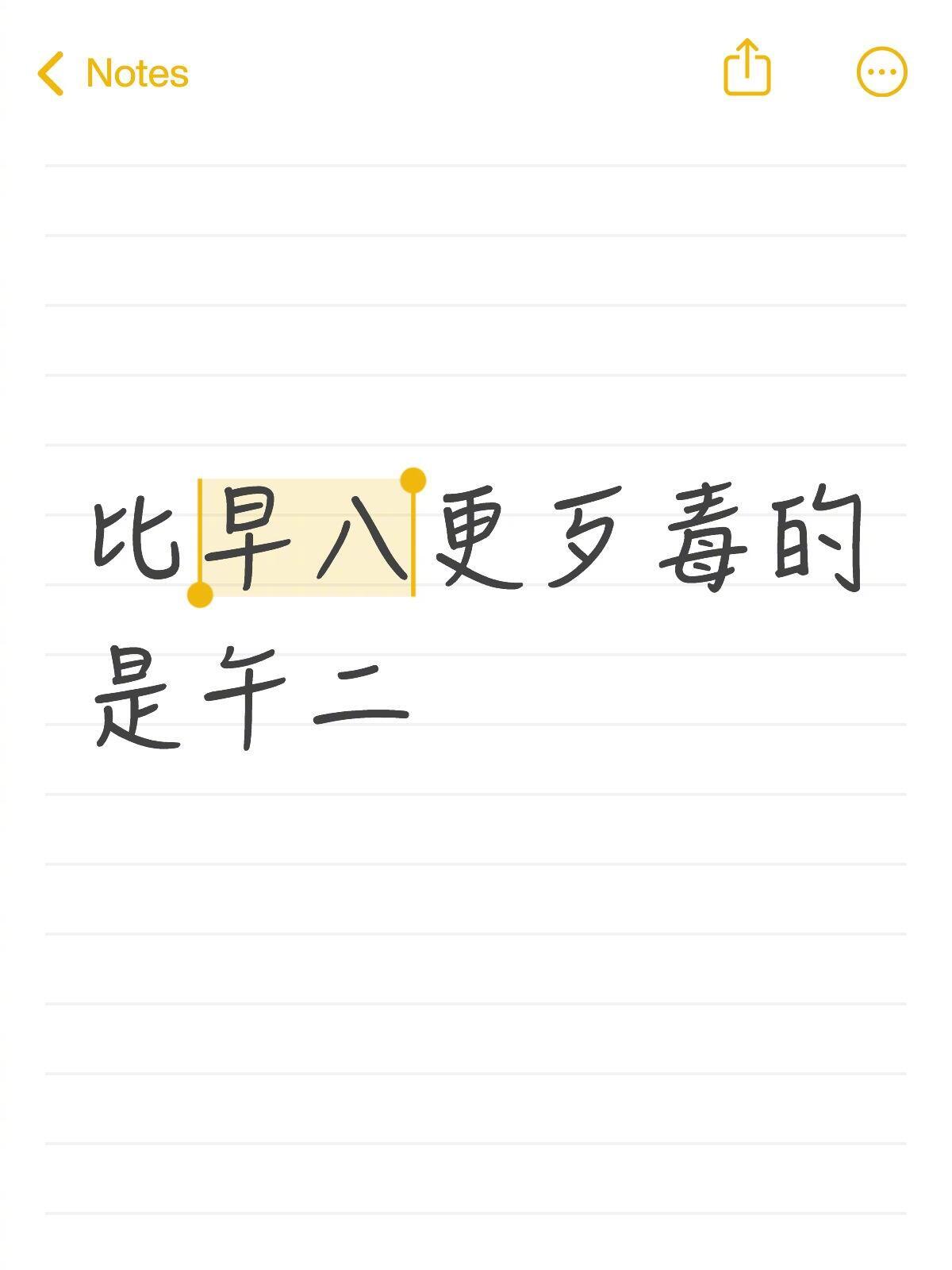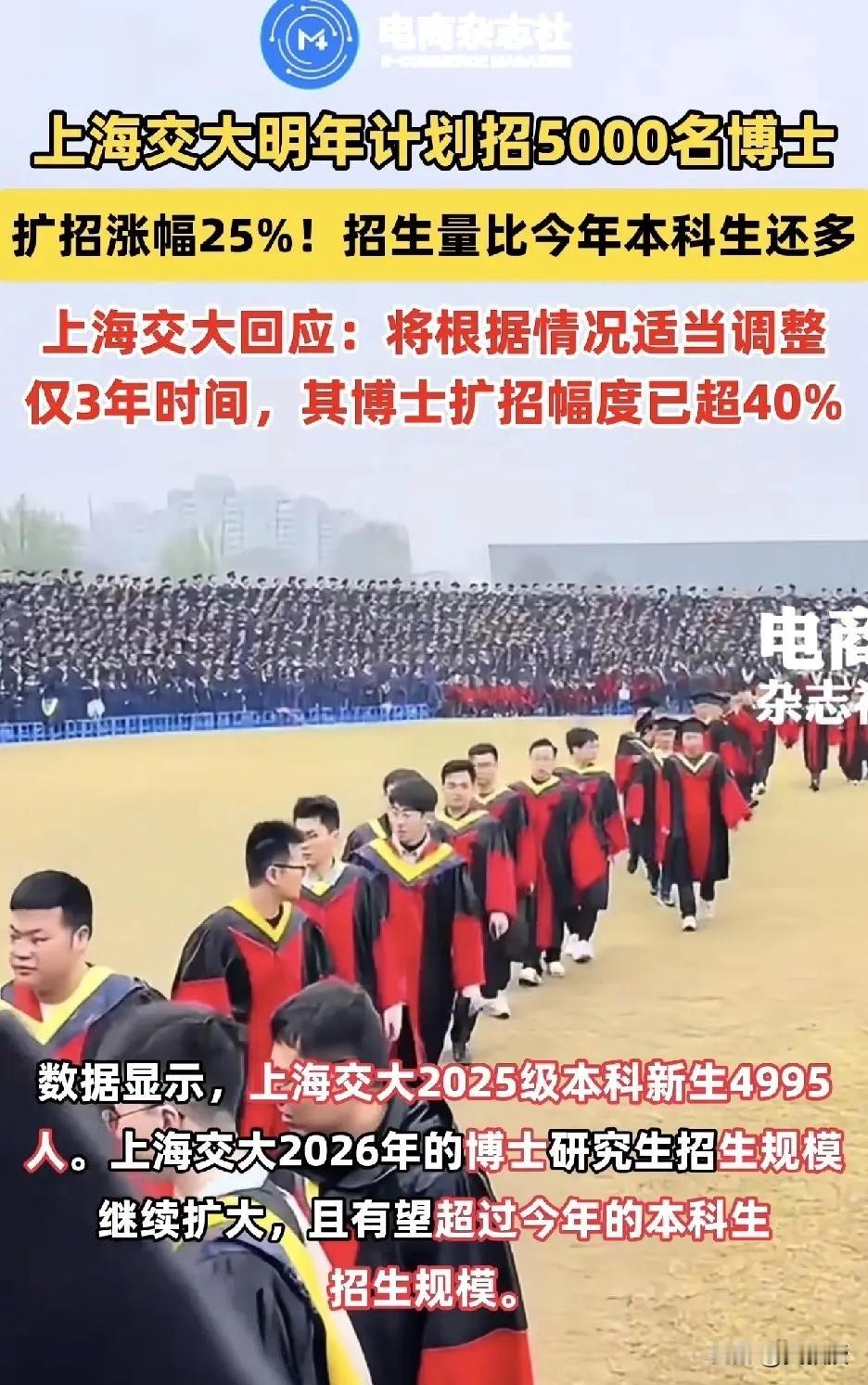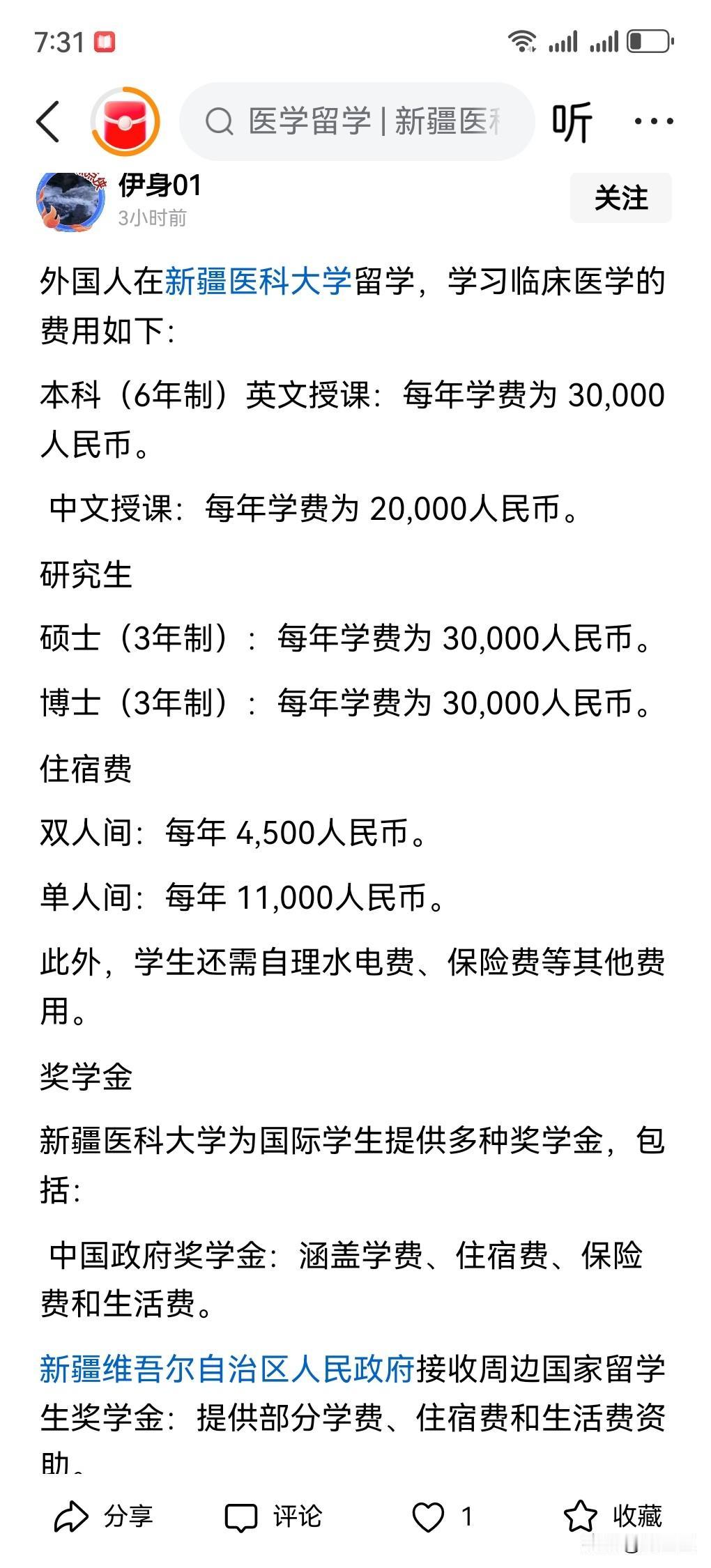为这位女研究生深感伤心!她是农学女硕士,因工作难找去农村创业,种草莓却受到种种刁难,最终结局大快人心。 10月中下旬,贺贺蹲在垄边,指尖抚过刚缓苗的草莓苗,眼泪却顺着沾满泥土的脸颊往下掉。 大棚角落还堆着房东没清理的杂物,远处约定好的灌溉池塘里,房东的鱼苗正欢快地游动。 那是她每年花一万元租来的“资产”,如今没一样能用得上。 这位怀揣“用知识改变家乡”梦想的农学硕士,怎么也没想到,返乡创业的第一课,竟是人情世故给的“当头一棒”。 贺贺的创业初心很纯粹,读硕士时,她跟着导师做草莓种植课题,培育的新品种在试验田里表现出众。 毕业后,看着家乡的土地大多种着传统作物,她揣着导师的技术资料和东拼西凑的启动资金回了村。 经同村长辈介绍,她和村民老李签了合同,以每年一万元的价格租下1.8亩地、两个大棚和一口池塘,长辈说老李为人实在,我连实地核查都没细做,就签了字。 合同刚生效,现实就给了她沉重一击,约定的1.8亩地实际丈量只有1.5亩,还全是寸草不生的荒坡,她雇人翻地平整就花了两千多。 两个大棚更成了“杂物仓库”,塑料布、破旧农具堆得满满当当,清理出的垃圾装了整整三车。 最让她窝火的是池塘,老李说“养鱼先占着水”,死活不让她用于灌溉,贺贺只能花钱拉水管解决浇水问题。 更糟的还在后面,老李的老伴主动找上门,说要帮她给工人做饭,开口就要每天300元。 贺贺算了笔账,工人一天工资才200元,这要求实在离谱,只能婉拒。没 成想,隔天大棚的电线就被“不小心”弄断了,老李说“电工不好找”,让她再请老伴帮忙“顺便看顾”。 就连她雇来卸货的村民,见她年轻好说话,卸到一半就坐地起价,多要200元才肯继续干。 那些日子,贺贺白天顶着太阳侍弄草莓苗,晚上还要跟老李夫妻俩掰扯权益,常常躲在大棚里偷偷哭。 她试着找介绍人调解,对方却劝她“忍忍就好,都是乡里乡亲”。 直到一次老李没打招呼就往大棚里打除草剂,要她付200元“工时费”,贺贺终于忍无可忍,找到了村书记和镇里的司法所。 好在贺贺的维权有了转机,司法所工作人员调取合同后发现,条款只写了租赁标的,没明确质量标准和使用权细节。 他们一方面给老李讲法律条文,明确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另一方面也帮贺贺联系农业农村局,争取到了创业指导补贴。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老李退还半年租金,清理大棚杂物并保证池塘使用权,贺贺则雇佣老李的儿子参与草莓种植,按市场价付工资。 贺贺的经历戳中了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人才下乡不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有温度的人文环境。 正如农业专家所说,“技术落地需要适宜的土壤,这个土壤既包括土地,也包括人文环境”。 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单靠创业者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乡亲们放下“小算盘”,拿出共发展的诚意;需要基层组织筑牢权益保障的防线,让创业者敢闯敢干。 当贺贺的草莓大棚里再次响起笑声,不难明白:乡村振兴的真正底色,从来都是让每一个返乡追梦的人,都能安心扎根、放心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