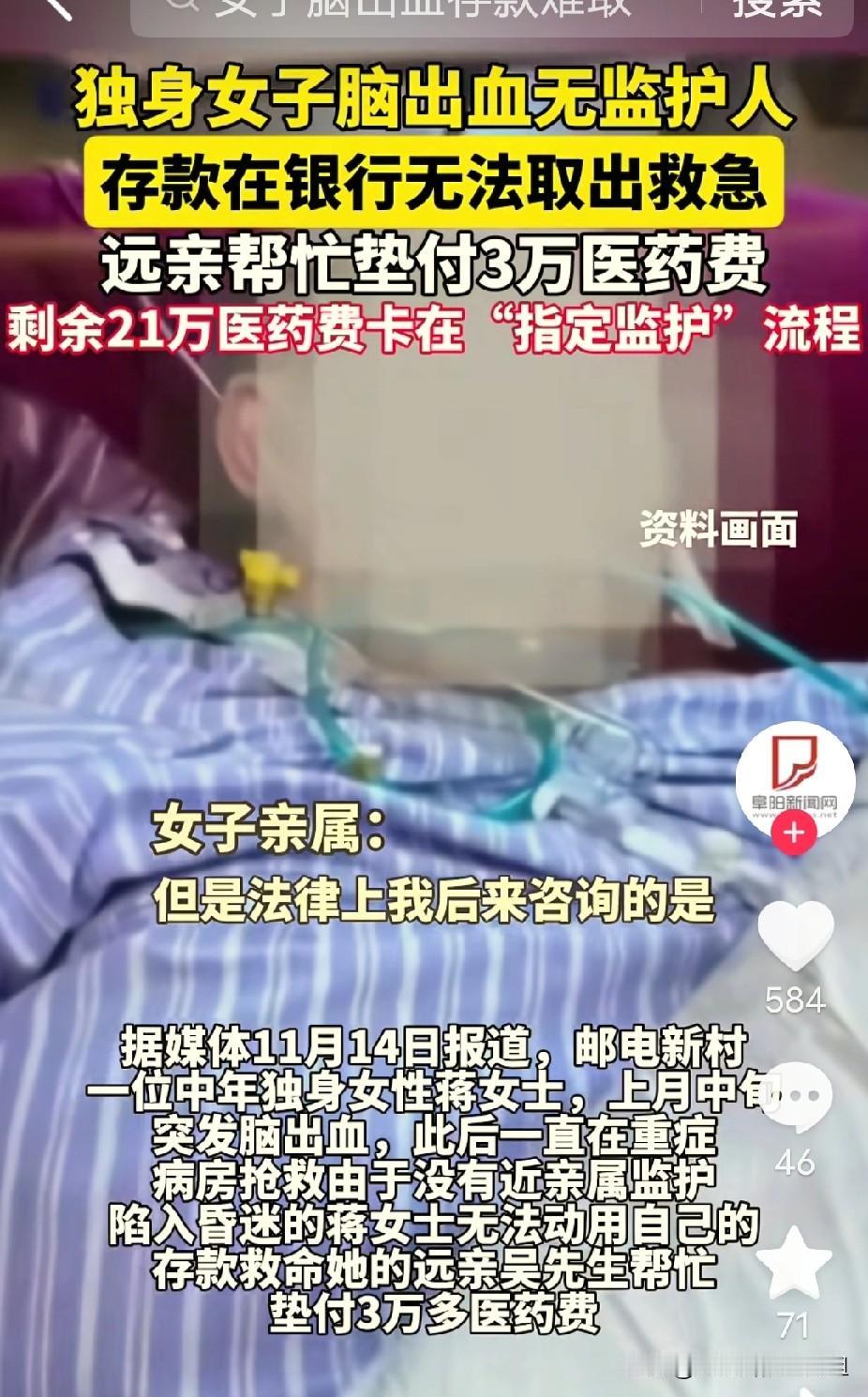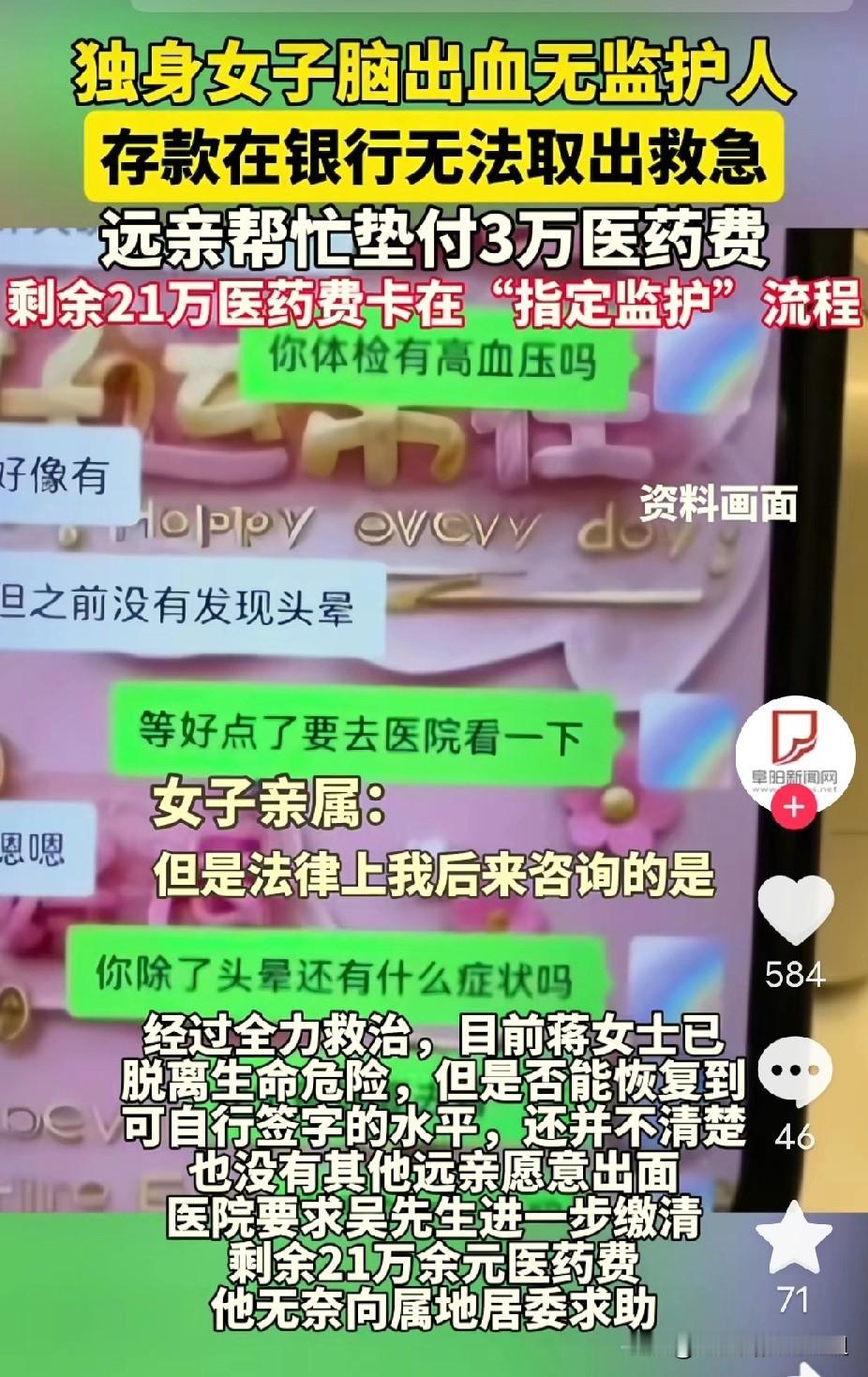上海,46岁的蒋女士突发脑溢血,可她未婚未育,父母又已离世,无奈之下只好找她的远房亲戚吴先生签字做手术。吴先生垫付了3万元的费用,可医院又要求他继续缴纳欠下的21万余元医疗费,吴先生承担不起,想让居委会成为蒋女士的监护人,居委会也很愿意承担,于是联系蒋女士所投重疾险公司及她的工资存放银行,想先拿钱给蒋女士治病,可对方均表示,居委会没有权利。 蒋女士的存折就在家里躺着,保险公司理赔金也早就准备好了,可这些钱就是卡在半空中取不出来。银行和保险公司咬死一条规定:必须得出具法定监护人证明。居委会王书记跑断了腿,得到的回复冰冷又坚决——“按照规定,你们确实没这个权限”。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蒋女士昏迷不醒所以需要监护人,但指定监护人需要她本人或近亲属申请,偏偏她什么都没有。 吴先生的处境更让人心疼。他出于善意签字垫钱,结果差点被21万医疗费拖垮。从法律角度看,他和蒋女士只是远亲,没有继承关系,万一蒋女士有个三长两短,他垫的钱可能都要不回来。这种好人难做的困境,以后谁还敢伸手帮一把?法律本该保护善意,现实却让好心人寒了心。 这事儿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还存在不少漏洞。随着单身人群和丁克家庭越来越多,每个城市可能都有成千上万个“蒋女士”。他们能工作、有存款、买保险,可一旦倒下,这些保障都可能因为一纸文书而失效。法律规定了居委会或民政局可以担任监护人,但具体怎么操作、需要哪些手续,很多基层单位自己都搞不清楚。 好在邮电新村居委会这次选择了“向前一步”。他们跑去法院梳理流程,准备先申请宣告蒋女士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再争取监护权。这个方案虽然能解决问题,但太费周折了。危急关头,生命通道不该被繁琐的程序堵死。或许可以学习某些国家的经验,设立紧急公共监护基金,或者授权医院在特定情况下先行处置患者财产用于救命。 这件事给我们每个人都提了个醒。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可能存在的远方表亲或程序复杂的公共监护上,不如趁自己清醒时通过“意定监护”指定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这不仅是一纸协议,更是把生命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