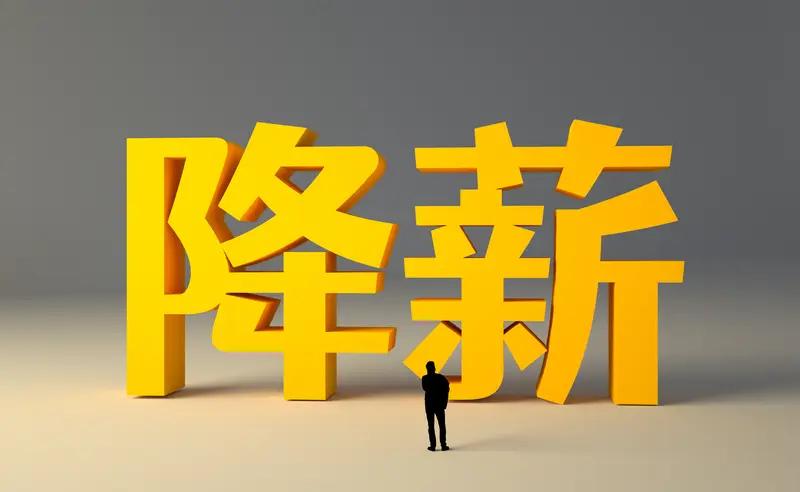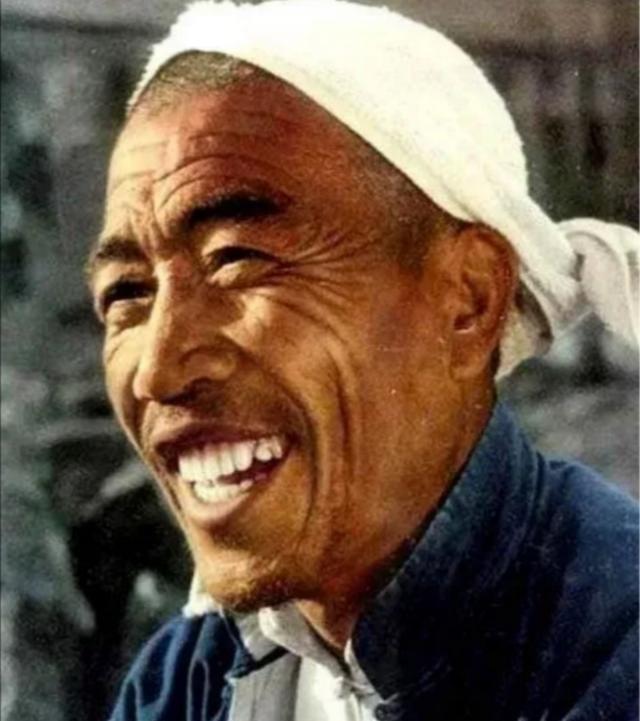1987年,一个女医生被哨兵拦住,要求出示通行证,没想到,她直接掏出一颗手榴弹:“这就是我的通行证!” 枪声在边境线上断断续续地响着,空气里混杂着焦土的味道。年轻的女军医刘亚玲背着急救包,推着担架车,正要穿越哨卡。哨兵横枪拦住她,语气严厉:“前线要通行证。 ”她面不改色,从军挎包里摸出一枚手榴弹,放在掌心,冷冷地说:“这就是我的通行证。” 那一刻,风停了,哨兵愣在原地。他看着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眼神坚定得像钢铁。半晌,他抬起枪,敬了个礼:“同志,请通行!”刘亚玲背起药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火线。 她心里清楚,那枚手榴弹不是用来威胁的,而是战地医生最后的尊严——如果被俘,她宁愿以死保密。 这位女医生出生在1963年的陕西宝鸡,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少年时的她,就常跟在村里的老医生后面帮忙递针线、烧药水。那时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能救人,多好。”1982年,她考入军医大学。别人都盼着分配到条件好的医院,她却主动申请去最前线的野战医疗队。 可领导不同意,说她太年轻、经验不足。她写了一份又一份申请书,连队里人都笑她“脑子进水”,可她的回答只有一句:“我学医,是为救人,不是为安稳。” 1986年冬天,她终于找到机会。以“回家探亲”为名,她搭乘运送物资的车队去了云南边境。当时中越边境局势紧张,许多伤员从前线被送下。她一到就开始抢救,一个接一个,衣服都被血染透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几乎每一次救治都像与死神赛跑。一次,她跪在山沟里,给一个腹部中弹的战士做止血,血浸满了她的袖子。战士的嘴唇发白,还强撑着说:“大夫,我不冷。”刘亚玲红着眼,压着伤口大喊:“撑住,等我把你送回去!”那一夜,她整整没合眼。 有人问她怕不怕死。她笑了笑:“怕,可更怕看他们死。”那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 一次夜间转移,刘亚玲的小腿被流弹擦伤,鲜血从裤管渗出。她没吭声,继续帮战士包扎。直到二十多个小时后,她在手术帐篷里昏倒。医生剪开她的裤脚,发现伤口早已化脓发黑。她烧到四十度,仍死死攥着笔,记录着每一个伤员的名字。 那一年,她才23岁。 1987年,她被调回后方疗养。组织给了她嘉奖信,夸她“舍生忘死,医者仁心”。同事劝她留下来,“以后有个安稳的岗位。”她没答话,只笑着说:“我还年轻,还有该去的地方。” 回国后的日子,她选择继续深造。别人以为她会进入大医院当专家,她却在2004年回到老家,用所有积蓄建了一所小诊所——村民付不起的医药费,她免;有老人送她鸡蛋,她推回去:“您自己留着吃。” 她始终坚信:“医生的价值,不在于治好多少人,而在于不放弃每一个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刘亚玲已是中年,仍带队连夜赶工生产消毒液。三百吨药液被分送全国,其中三十吨送往武汉。有人劝她休息,她笑说:“我在战场上都没怕过病毒。” 这一句话,让身边的年轻医生都红了眼。 她一生经历过枪林弹雨,也熬过无数个没有电的夜晚。可她从未抱怨一句。她常对学生说:“医学,不是职业,是信仰。” 后来,她的故事被写进军队档案。有人称她是“新时代的南丁格尔”,可她只是淡淡地笑:“我是刘亚玲,一个普通军医。” 有人问她当年那枚手榴弹还在不在。她点点头,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布包,里头静静躺着那颗锈迹斑斑的手榴弹。她轻声说:“它见过我最勇敢的一面,也提醒我,救人要有不怕死的心。” 她这一生,跨过硝烟,也跨过岁月,用手术刀和心守护了无数生命。 “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活了多久,而在于他为别人活了多少。”——托尔斯泰的这句话,或许正是她最好的注脚。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以一枚手榴弹为通行证,用青春和热血打开了通往生命的通道。那一抹白色的身影,从未在战场上消失,也从未在历史中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