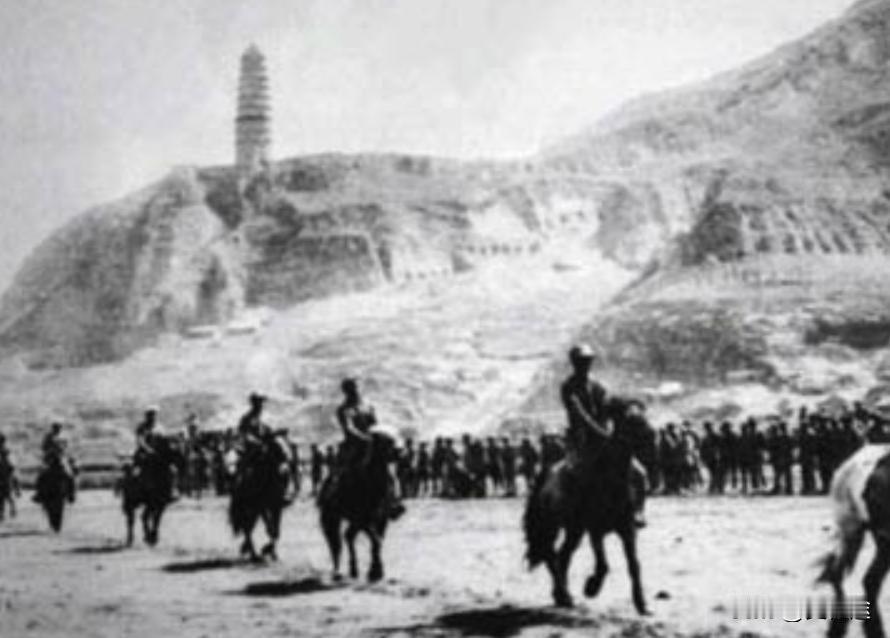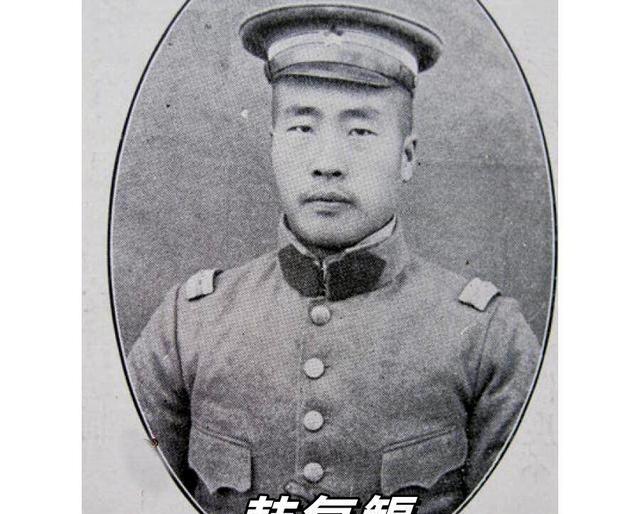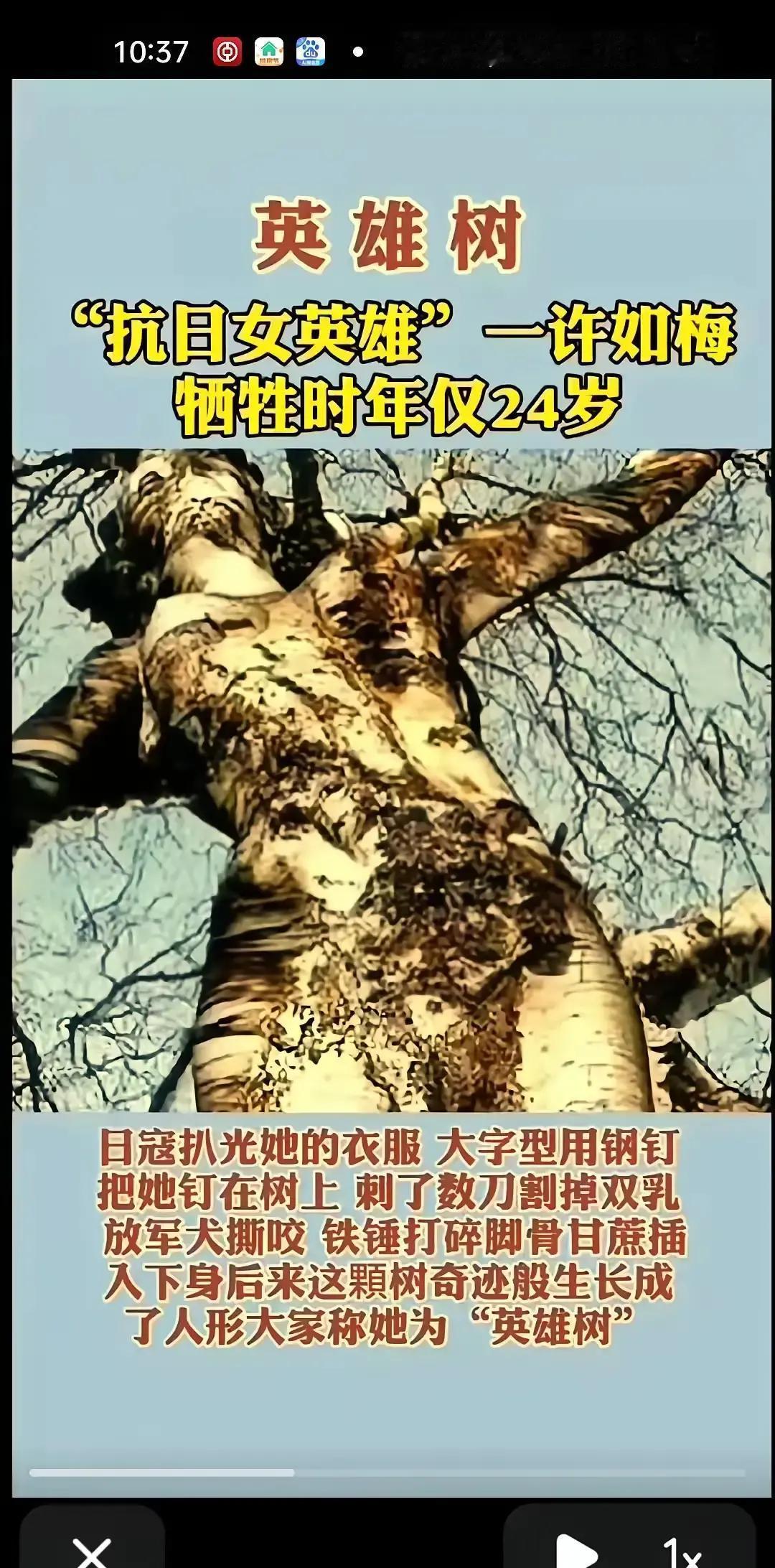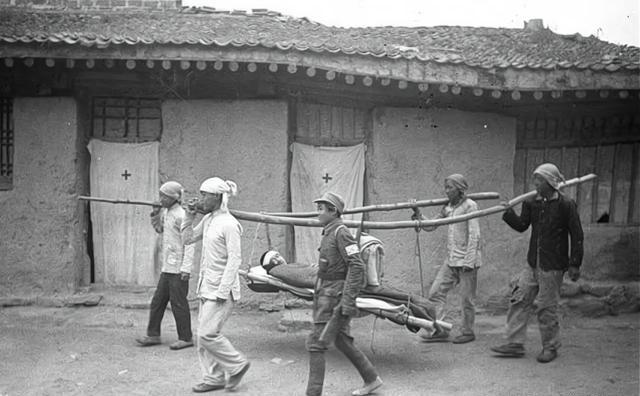抗战时期,日军为什么没有攻占延安。 一句话:没有实力攻占。 若有这个实力,日军早就攻占了。 抗战那几年,延安天天在炸。 自一九三八年前后起,日军轰炸机一趟接一趟飞来,三年间扔下去的重磅炸弹加起来过了一千枚,城墙倒了,街口塌了。 新中华报的战报却只好写上一句:“民房一百多间,猪两头,鸡几只,人命损失很小。”机关和老百姓早搬进山体窑洞,几丈黄土顶在头顶,炸弹砸过来,黄土抖一抖,洞里灯还亮着。 这种怪模样落在东京眼里,很扎心。 有些人随口一句“陕西穷,日本人懒得打”,还有人爱编什么“心照不宣”的说法。史料里给出的画面要冷硬得多。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有八路军的军校,国民党在汉中也有黄埔分校,对日本参谋本部来说,这一块在中国地图上,只能排在重庆后面,绝不是可以随手放过的偏角。 要追问日军为什么没攻下延安,得从东北算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沈阳北大营被偷袭,张学良执行“不抵抗”,东北防线很快崩塌。 一九三二年前后,伪满洲国被扶起来,老张家的军工厂被接收,火炮、子弹、钢板从东三省源源不断送出,那里成了侵华的大后方。 一九三七年,日本自觉条件成熟,在华北、华中发动全面战争,大声喊出“三个月灭亡中国”。 问题在于国力。日本本土面积有限,资源紧巴,仗一开,兵就被一块块钉死。 朝鲜要驻军,东北要驻军,华北、华中、华南的铁路、港口、矿山也要人守。 到了一九三九年前后,有估算说,日本在中国战场真正能机动的兵力不超过三十万,其余多半散在各地“看门”。这一年,东京高层已经看明白,速胜无望,再加码只会陷进去,只能把眼光转到东南亚那一堆石油和橡胶上。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方向开火,日本又得抽兵去对付新的对手,中国战场一下被挤在边上。 关东军要兵,中国派遣军要兵,南线要兵,轮到专门为陕西、为延安筹集一支大兵团时,手里的筹码已经所剩无几。 纸面上看还有余地,参谋真正把棋子摆到地图上,就只能苦笑。 就算真省出兵来也得过地形这一关。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青藏高原在最上,东部平原在最下,中间一层是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秦岭。陕西就趴在这一层,黄河以西、秦岭以北,对坦克、卡车来说,这里是一片黏糊糊的泥地。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日军在黄河一线发动过七十多次渡河行动,工兵搭浮桥,守军端着火炮在岸上等,浮桥刚接好,就被火力和急流拆得七零八落。 永济一带那次算是典型。 守军提前把渡船凿沉,日军只好亲自搭桥,桥身刚到河心就被洪水掀翻,连人带炮车掉进黄河,一个中队被卷得不成样子。 几番折腾,日军对“硬闯黄河”心里开始打鼓。就算过了河,前头还有潼关这道口子。 这里山道狭窄,国民党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压在一线,坦克在山腰上排成长龙,展开不开,退也难退,重炮被卡在拐弯处,只能当靶子挨打。一九四二年,日本曾研究从潼关打进陕西、再南下川渝的方案,算到兵力和补给,只能把卷宗压回去。 往西北看,是陕甘宁那一大片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日军飞行员在一九三八年冬天的侦察报告里写过一句顺嘴的话,说那一带“山像被爪子抓过,沟比路多,坦克进去就是铁棺材”。 这句评价进了日本参谋本部档案,摊在东京案头。 参谋拿尺子在地图上来回比划,前进方向上的等高线挤在一起,谁都明白,真把一个整师团丢进去,供给线拉得老长,再碰上游击队在后边捅几刀,想全身而退几乎是做梦。 延安周围也不是空地,一九三八年,日军第二十六师团抽出两千多人,带着二十多门火炮,准备在黄河一带强渡,八路军警备第六团等到日军渡到河心、队形挤在一起时,才压着扳机开火,这股兵力被打得七零八落。 没多久,日军加码到旅团规模,沿汾离公路往前挤,八路军第八团早埋伏在山坡两边,夜里冷枪一通,把那条机械化队伍敲成几截。 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对陕西方向搞过二十多次试探性进攻,陕北府谷一带曾短暂失守数小时,很快被收回。 真正让日本犯难的,是那一圈“看不见”的防线。 陕甘宁边区档案记着,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三年,登记在册的民兵有二十六万七千人,手里有四万二千多条土枪,一万一千多枚地雷,地下挖出三千七百里地道。 白天扛锄头,晚上扛枪,打一仗又散回村里,想抓干净根本不可能。 一边打仗,一边还得过日子。 南泥湾开荒不只是歌里好听,一九四二年前后,边区棉花自给率已经到六成多,纸张接近七八成,食盐甚至有盈余,最缺的是铜和化工原料。 兵工厂把坏钟、旧铜钱、破铜像丢进炉子里熔成零件,子弹虽然不多,配上熟门熟路的游击战、伏击战,却足够让日军在山路上处处掂量,“以战养战”的老路,在这片黄土上走不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伪满洲国垮了,华北不少城市经历了占领又收回,陕西这一块,从头到尾没进过日占区。 那座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黄土城,在窑洞灯火里站到终点,对那支自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军队来说,这里不是谁大发慈悲留下的空白,而是一块怎么算账都啃不动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