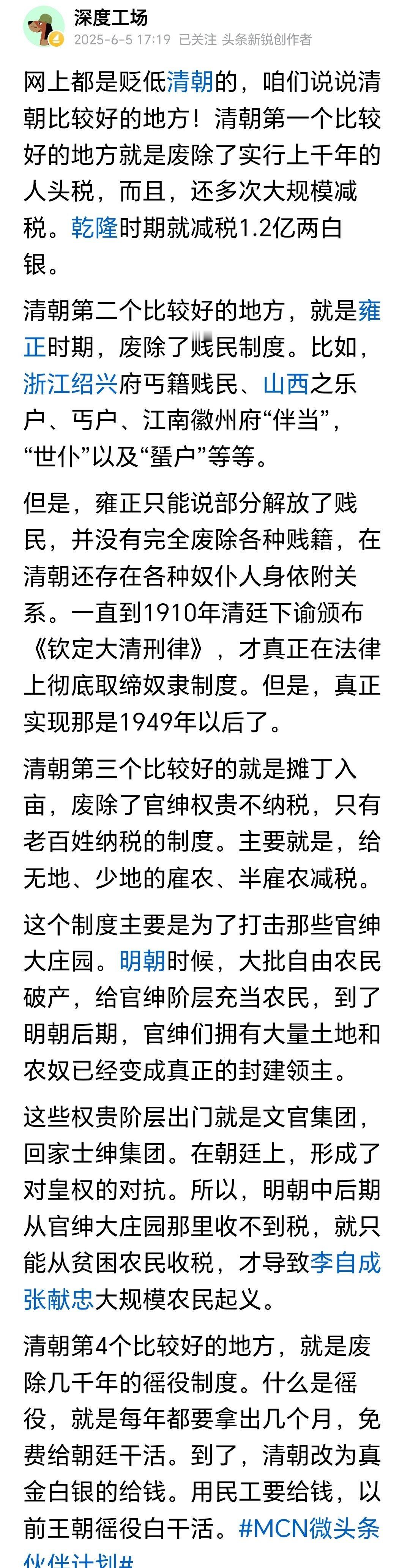他叫聂曦,身中七枪,壮烈牺牲! 1950年台湾党组织,因为被蔡孝乾出卖,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将领,他是上校级别,随着吴将军被抓,他一样被害了,牺牲前他目光如炬,勇敢赴义,身中七枪,壮烈牺牲。 他面对特务的残酷的刑罚,没有屈服,没有出卖组织,而是选择慷慨赴义!他的牺牲悲壮而崇高,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无数英雄负重前行! —— 枪声在台北川端桥边炸响,七颗子弹像七道闪电,把三十岁的聂曦钉进黎明前的黑暗。血顺着石缝往河里淌,把淡水河染成一条暗红的绸带。对岸的灯火还亮着,歌舞厅里《夜来香》正唱到高腔,没人知道这边刚结束一条命。特务踢了踢尸体,确认没气,才叼着烟往车里钻,车轮碾过血泊,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随意。 可他们没看见,聂曦倒下前嘴角带着笑,那笑像把刀,插在蔡孝乾的眼皮底下——出卖者当晚就做了噩梦,梦见七颗子弹排着队钻进自己脑袋,醒来裤裆湿了一大片。 把时间往前拨半年,南京路一家裁缝铺的阁楼,聂曦正给吴石将军缝最后一颗扣子。窗外雨声敲铁皮,像无数小鼓。吴石低声说:“老聂,要是哪天我先走,你别学我写字留遗言,太文绉绉,咱们军人,留点血就够了。”聂曦咧嘴:“将军,你留遗言,我留子弹,看谁先请对方喝酒。”两人相视大笑,笑得像明天就能回家抱孩子。谁料分别真就是永别,吴石先被拖进刑场,聂曦后脚跟进,中间只隔了十七天。 蔡孝乾的叛变像一把钝刀,慢慢锯断整个台湾省委的喉咙。这老头儿当年也在延安啃过窝头,回台湾却迷上日式料理和美国威士忌,把信仰当旧衣服扔给洗衣店。他供出的人名写满三十页纸,每页都血迹斑斑。聂曦的名字排在中间,旁边画了个红圈,特务头子叶翔之在旁边批注:“上将之材,可惜不听话。” 抓人的那晚,聂曦正在家里给孩子洗尿布。老婆坐月子,他笨手笨脚,把香皂打成鸭子形状哄儿子笑。门被砸开,十几支手枪对准婴儿床。聂曦举起湿哒哒的双手,回头对老婆说了句台语:“忍耐一下,我很快转来。”老婆哭到昏厥,孩子突然不哭了,瞪大眼睛望着父亲,像要把这张脸刻进DNA。 审讯室在警总后院,原先是日本宪兵队养狼狗的地方,墙上还留着昭和年间的铁环。聂曦被吊在铁环上,脚尖刚好够着地,像跳一场永远跳不完的芭蕾。特务把竹签钉进指甲缝,边钉边问:“吴石把情报藏哪?”聂曦疼得浑身打摆子,却用闽南语骂:“干你娘,藏在你祖坟里,自己去挖。”竹签断了,换烧红的铁条,肉香混着焦糊味飘出窗外,隔壁关押的学生开始呕吐。 第三天夜里,审他的人换了,是个穿西装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说话软绵绵:“聂上校,你在日本陆军大学拿过第一名,蒋总统都说你是‘芝兰玉树’,何必为对岸卖命?只要你写个自白书,我保你当少将,再批一栋阳明山的洋房。”聂曦抬起头,肿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突然闪出光:“小子,你知道我为啥取名叫曦?我阿公说,晨曦的曦,是黑夜的最后一刀。你们天快亮了,但刀还在我手里。”说完一口血啐在对方白衬衫上,像开出一朵梅花。 行刑前夜,特务给他送来烧酒卤味,说是“上路饭”。聂曦把猪脚啃得干干净净,骨头排成一排,小声哼《义勇军进行曲》,哼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声音突然拔高,看守吓得一哆嗦,枪都掉地上。他笑:“别紧张,老子不跑,老子只是先把号子练起来,到时候好集合。” 枪响那一刻,台北的天空刚好泛起蟹壳青。第一颗子弹打穿左胸,他往前冲;第二颗打断腿骨,他跪地仍挺腰;第三颗第四颗钻进腹腔,血像喷泉;第五颗第六颗打在肩膀,手臂垂下却握拳;第七颗从右太阳穴进去,左眼眶出来,眼球挂在脸颊,像一颗不肯闭上的星星。尸体被踢进预挖的土坑,特务铲土时,那只挂在外面的眼球突然眨了一下,吓得铲土的小兵当场疯掉,后半辈子见人就喊“他看我!他看我!”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可历史总爱留尾巴。聂曦的儿子后来偷渡到香港,身上只带一张父亲穿军装的照片。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爸爸去出差,很快回来。”儿子把照片装进塑料袋,再套一层塑料袋,一层又一层,像给记忆穿防弹衣。三十年后,他作为台商回到福州,在马尾码头对着台湾方向跪下,把照片一张张烧给海风,边烧边说:“爸,你讲的很快,真的好快,快到我头发都白了。” 有人问我,写这些陈年血案图啥?又不能让死人复活。我说,图个“记得”。记得有人用三十岁的命换我们今天的夜宵摊能开到凌晨两点,换我们能大摇大摆刷手机骂老板。记得背叛者也能写回忆录,还能拿稿费,而忠臣连块墓碑都得刻假名。记得“祖国统一”不是新闻联播里的四个字,是七颗子弹、三十页供词、一堆碎指甲和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