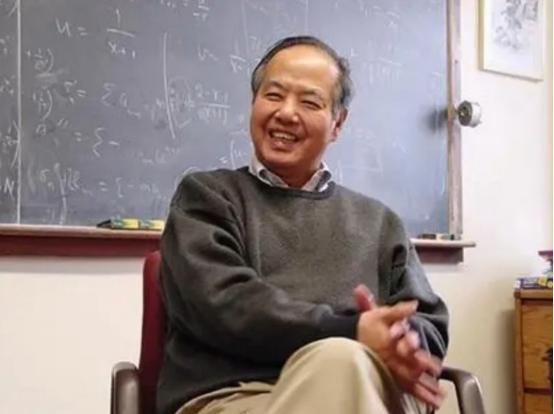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1946年的芝加哥大学,刚从中国辗转而来的李政道坐在费米的办公室里,突然,对面的费米开口问了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 李政道想都没想就报出了书本上的数字,可费米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一个标准答案,为何换来了批评? 那时的李政道刚在恩师吴大猷、叶企孙的推荐下赴美求学,芝加哥大学是唯一愿意接纳他直接进入研究生课程的学校。 费米当时已是物理界泰斗,正忙着建造粒子回旋加速器,测量中子—电子相互作用,原本并不打算带理论学生,最终却破例收下了李政道,还每周抽出半天时间,专门和他讨论问题。 他们的交流总有种特别的模式:费米会提前给李政道指定课题,让他读透文献后再“反过来”给自己讲课,用这种方式训练他的独立思考能力。 太阳温度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突然冒出来的。 李政道报出的“1000万度”并非随口乱说,而是当时文献里常见的数值,只是他从没想着去核实。 因为那些关联光强和能量产生的方程太过复杂,对当时专注于其他课题的他来说,似乎没必要花功夫深究。 可费米偏要在这个“小问题”上较真,反复追问他是否自己计算过,直到李政道坦言“没有”,便立刻给出了严厉的批评。 没人能想到,这位忙着做高能物理实验的大科学家,会为了一个和自己研究无关的问题花心思。 费米没让李政道死磕复杂公式,反而拉着他一起动手做工具,他亲自动手做木匠活,李政道则负责刻制标尺、摄影放大对数刻度。 花了好几天时间,做成了一把六英尺长的大计算尺——这是世界上唯一专门用来计算太阳温度的计算尺。 有了这把特制工具,原本繁复的微分方程运算变得简单,李政道只用一个小时就算出了结果,和书本上的1000万度相差无几,之后又花一天时间算出了太阳半径上一百多个位置的数据。 费米当时的课题和太阳温度毫无关联,他这么做只为传递一个简单的道理:做学问不能盲目接受他人的结论,所用的公式和数据,都必须是自己独立推导并验证过的。 这种教育方式贯穿了李政道的求学时光。 后来费米还曾让李政道研究玛丽亚·迈耶的壳层模型,当李政道坦言没有进展时,费米甚至提出“互换角色”,让李政道给自已讲课,用这种方式引导他突破瓶颈。 那次计算太阳温度的经历,像一颗种子在李政道心里扎了根。 后来他和杨振宁研究θ–τ之谜时,始终记得费米的教诲,不仅全面核查了所有所谓“支持宇称守恒”的实验证据,发现其实没有真正的验证依据,还明确提出需要通过专门实验来检验。 而当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他们“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说后,短短一个月内近百项实验跟进验证,这种快速突破的背后,正是对“独立验证”原则的坚守。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凭借这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多年后,李政道还保存着那把计算尺的照片,也常向人提起这段往事。 他回国推动建立少年班、博士后制度,以及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时,总不忘强调基础科学研究中“亲手验证”的重要性。 他在给国内领导人的建议里提到“基础科学是水”,而这汪水的源头,或许就藏在费米那句批评和那把特制计算尺里。 有人说费米是在吹毛求疵,毕竟李政道报出的数值并不算错。 但真正的科学精神,从来不是记住标准答案那么简单,费米批评的不是那个“1000万度”的数字,而是那种“拿来就用”的思维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