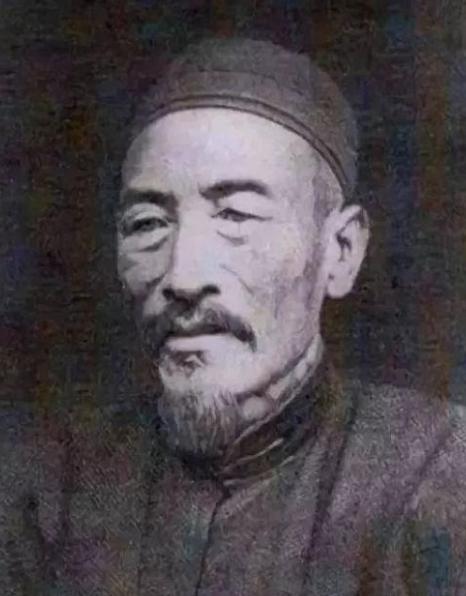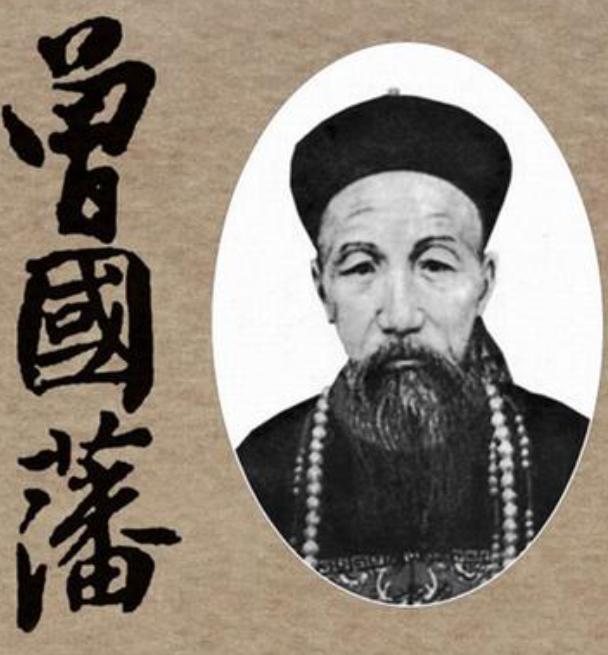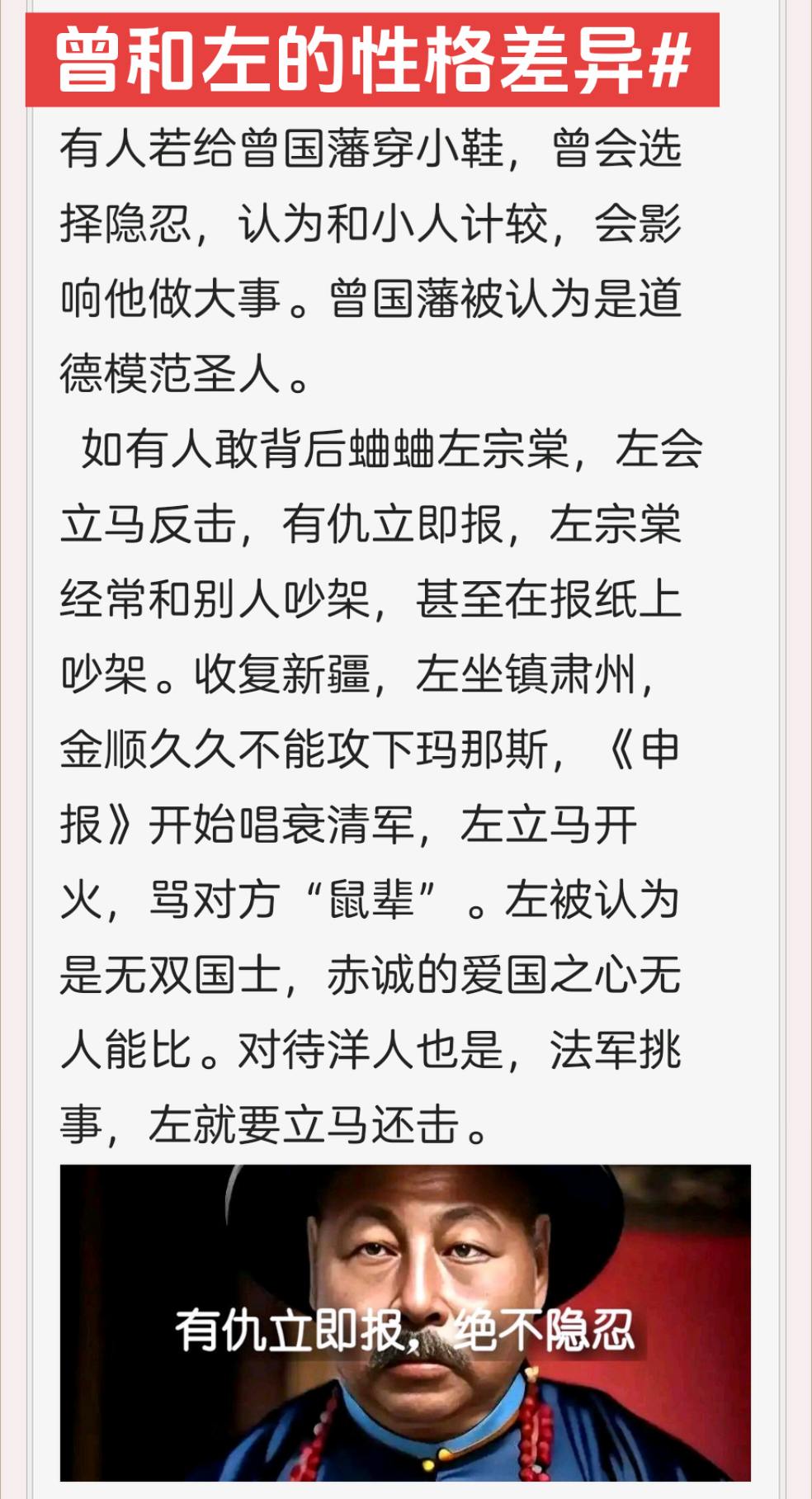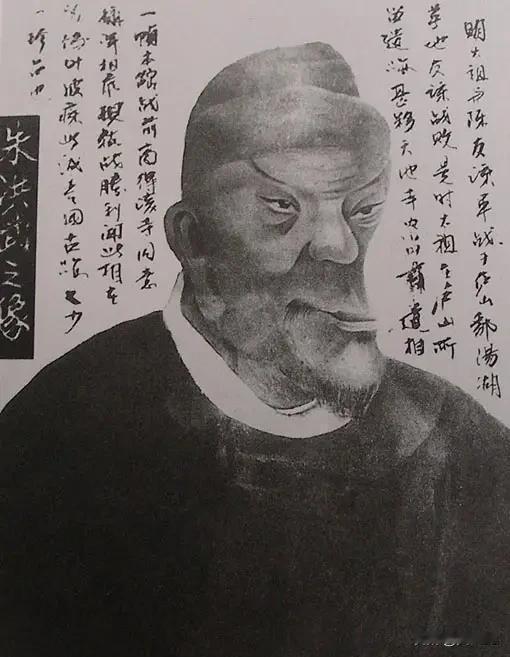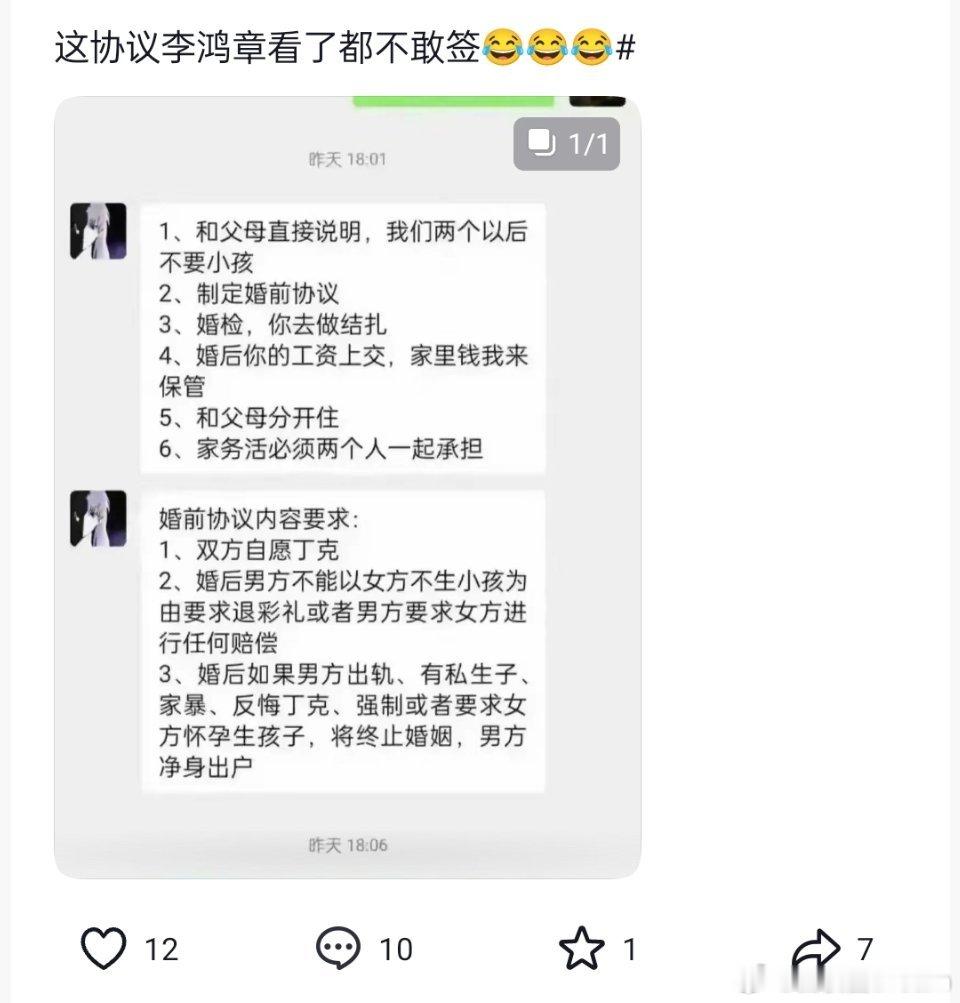轰动西方的中国奇人,如果他早生100年,整个中国都会翻天覆地! 1881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翻译徐涛的论文发表在了《自然》上,那年西方科学圈像被泼了冷水。论文里,徐寿质疑物理学家丁铎尔所著《声学》中关于 “有底管、无底管发出声音的震动数皆与管的长度成反比” 的声学结论,还把中国古代声学的老知识摆上国际舞台,通篇没有洋腔洋调,只有实打实的实验数据和中式逻辑。 当时英国皇家学会有人直接把论文复印件扔进壁炉,但没多久,欧洲一票学者开始翻查中国古书,试图找出徐寿嘴里的源头。国际科学界第一次认真琢磨起“中西合璧”这几个字。那段时间,伦敦的学术沙龙、巴黎的咖啡馆、柏林的讲堂里,徐寿成了热门话题。 很多年后,历史学家称徐寿是中国科技第一人。因为他不仅造蒸汽机、建造船厂,还把满满一本本西方科技书翻译成了中国字。他玩的是跨界,拼的是命。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如果他早生一百年,或许大清早就不是那个大清了,整张中国科技地图都会换模样。 徐寿小时候是无锡望族的“读书种子”,家里书香门第,父亲盼他中举光宗耀祖。可徐寿自小讨厌死八股文,每次背书都能把老师气得摔书。他喜欢拆钟表、画图纸,甚至会拉着村里的铁匠磨水晶做三棱镜。 别的孩子在背四书五经时,他琢磨着怎么让小钟自己报时。22岁那年,家里给他最后通牒,要么考中举人,要么自谋出路。徐寿想都没想,扔下考卷,回家拆钟表,动手做象限仪。乡里人说他脑子有病,徐寿却乐在其中。 白天跟着工匠学磨刀,晚上自己琢磨西洋轮船的结构,他翻烂了《博物新编》,还真照着书上的图纸造了个小型蒸汽机。没人看好他,家里都觉得他在瞎胡闹。可正是这些“折腾”,让他练出一身过硬的动手本事,也让他后来成了晚清最懂工程的中国人。 后来有人翻查无锡地方志,发现徐寿小时候经常和打铁的、修表的、造船的混在一块。他学了不少传统工艺,心思细腻又爱琢磨。别人只会照本宣科,他却喜欢用手去摸,用眼去看。有人说他叛逆,但这股劲儿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因为他实在看不惯死读书那一套。他觉得,只有把知识用出来,才能算真本事。这种执念,和当时风气格格不入,也正是他后来能闯出奇迹的底气。 太平天国内乱,西方坚船利炮横扫长江,清廷这才发现自己造不出像样的机械。曾国藩在安庆设了内军械所,四处找人造蒸汽机。没人敢接这个活,只有徐寿点头。 那会儿,他手里只有一本《博物新编》,几张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图纸,和一堆没见过世面的工匠。三个月,零件全得自己磨,螺丝一颗颗敲出来。屋里只有蜡烛和铁锤声。徐寿眼眶熬红,手上全是油泥。工人们一开始还嘀咕他疯魔,后来见他连吃饭都在画图,慢慢服气了。 四年后,“黄鹄号”蒸汽船下水,那天江面上热闹极了,连外头的洋人都伸长脖子看有人鼓掌,有人流泪,更多人根本不相信这是一群中国人干出来的事。 后来徐寿又建造了“惠吉号”军舰,还提出“开煤炼铁”等大动作。可惜清廷一听要烧钱,立刻翻脸,朝堂上有人当众拍桌子,说这种事不合祖宗规矩,徐寿气得脸色像泡了半天的茶叶,黯淡又绵软。 这以后,徐寿把精力全投进了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译著共二十余种西方科技书,内容从化学、物理到矿学、兵学,什么都不落下。他翻译《化学鉴原》,把欧洲的“periodic table”翻成“元素周期表”,还亲自制定了一套命名规则,让中国学生一看就明白。 翻译时,他常和儿子徐建寅、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围着桌子争论术语。傅兰雅回忆,他们经常为一个化学名词吵到半夜,徐寿咬着烟杆不松口,非得争出个道理才作罢。 他请来上海滩最能折腾的老师,开设实验课,让学生亲手做实验,不再死记硬背。 1881年,徐寿的论文被翻译,投给了《自然》杂志。这篇文章,不只让西方科学家哑口无言,更让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也能拿出自己的东西和西方掰腕子。 可惜,清廷的守旧和社会的惯性,把徐寿的很多想法卡死在半路。明明眼前有路,偏有人非要回头走老路。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中国第一篇《Nature》论文,140年前就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