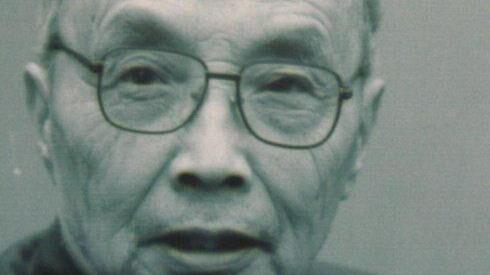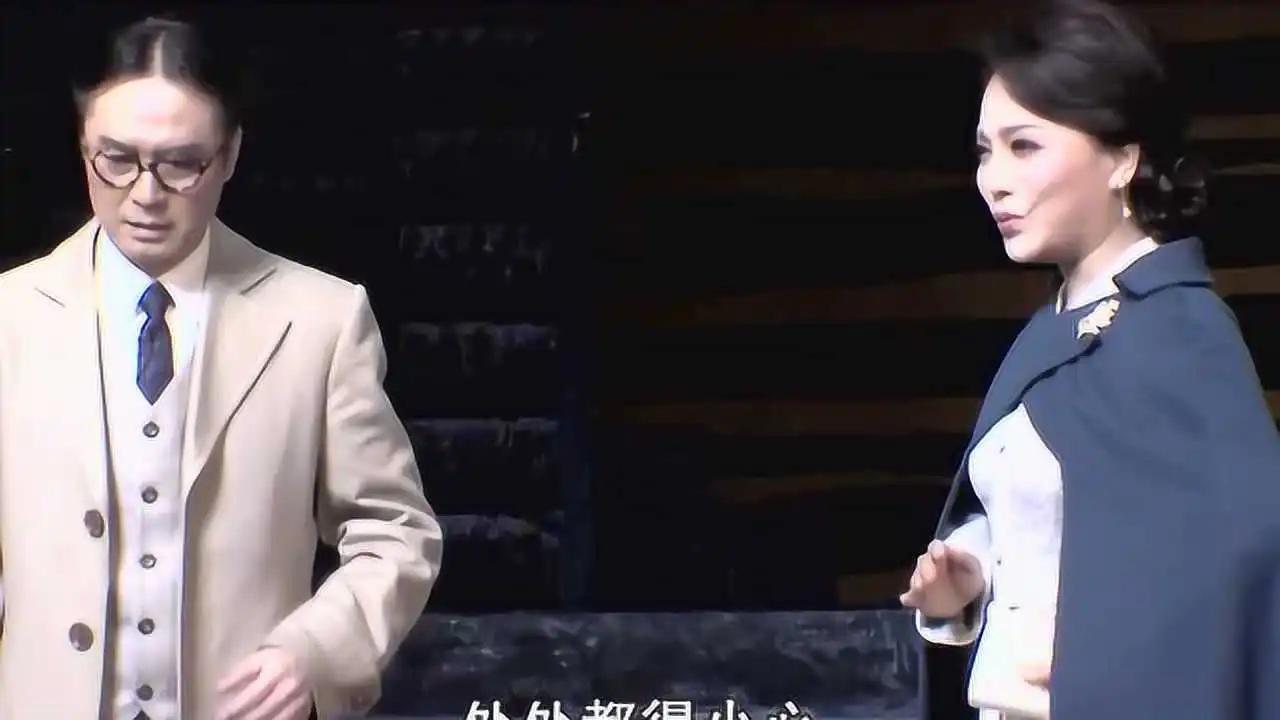1951 年的公审大会上,黄茂才被押到场中央。听到“判处死刑”的那一刻,他突然提高声音,喊出一句让所有人愣住的话——“我冤枉,我帮过江姐。” 周围的人一片哗然,可没人敢接话。他被迅速带离现场。这次喊冤为什么能改变结局?这件事背后的故事,比现场的混乱要复杂得多。 江姐被押进监室后,黄茂才每日负责巡查。他起初沉默寡言,不敢靠近这些“重点犯人”,可每天都能看到那些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人还在交谈、互相安慰。 他第一次注意到江姐,是她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另一名女同志有没有吃到早饭。简单的一句话,让他对这群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渣滓洞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守卫增加,检查更严。但黄茂才私底下却开始改变。他每次接到外出买食物的任务,都会把狱中同志写给外界的纸条藏在衣服里夹带出去,再带回外面报纸和讯息。 他知道,如果被发现,后果和革命志士没什么不同。他仍继续帮忙,因为那些纸条会让狱里的人知道战事进展,也能把家属的消息传回来。 有一次,狱中的女同志看到他穿着单薄的衬衣,悄悄把她们凑到的毛线交给江姐,由她组织大家轮流织成件毛衣。黄茂才收到那件毛衣时,愣住了。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人”。他因此更加小心,把每一次接触都当作最后一次机会。 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错失最关键的一刻。母亲病危的消息从老家传来,他请假离开渣滓洞。等他赶回重庆时,江姐已被杀害,七天后更爆发了“11·27”惨案。 他站在空荡的牢房前,听着消息,久久不动。没多久,他因遭特务怀疑“思想不稳”被辞退。他本以为事情可以从此平静,可 1951 年,他突然被带走,罪名是“参与迫害革命志士”。 他越辩解越被视为狡辩,所有记录都对他不利。直到公审现场,绝望压得他透不过气,于是那声喊冤脱口而出,成为让办案人员重新审视他的关键。 法院开始再调查,虽未立即获清白,却捡回了一条命。 从监狱释放后,他依旧背着沉重的“历史问题”。他本想用当年的毛衣证明自己的经历,可在被抄家时,那件衣物遗失,让他失去了最有力的证据。 事情的转机,从 1981 年的一份旧档案开始。重庆烈士陵园在整理史料时,发现一段关于渣滓洞看守暗中帮助革命志士的文字,记录与他高度吻合。纪念馆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又找到幸存的曾紫霞。 多年后重逢,曾紫霞一眼认出他,立即写下证明,说明黄茂才确实在渣滓洞多次冒险帮助革命同志。多位幸存者纷纷提供证言,事实逐渐清晰。 1982 年,法院正式撤销原判,宣布他无罪。压了他 28 年的负担终于落下。随后,他被聘为县政协委员,开始向学生讲述那段历史,把他亲眼见到的英勇事迹传递出去。 晚年的某一天,他重返渣滓洞旧址,站在曾经巡过无数次的走廊里,轻轻鞠躬。 倒推到最初的起点,他的人生从未顺遂。1925 年出生在佃农家庭的他,自小见惯饥苦。因为识字,比许多同龄人更容易被地主看中,从杂工到文书,再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他并非主动选择那条路,而是生活迫出的选择。直到在渣滓洞看到那些革命志士,他才第一次明白,“穷人能够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