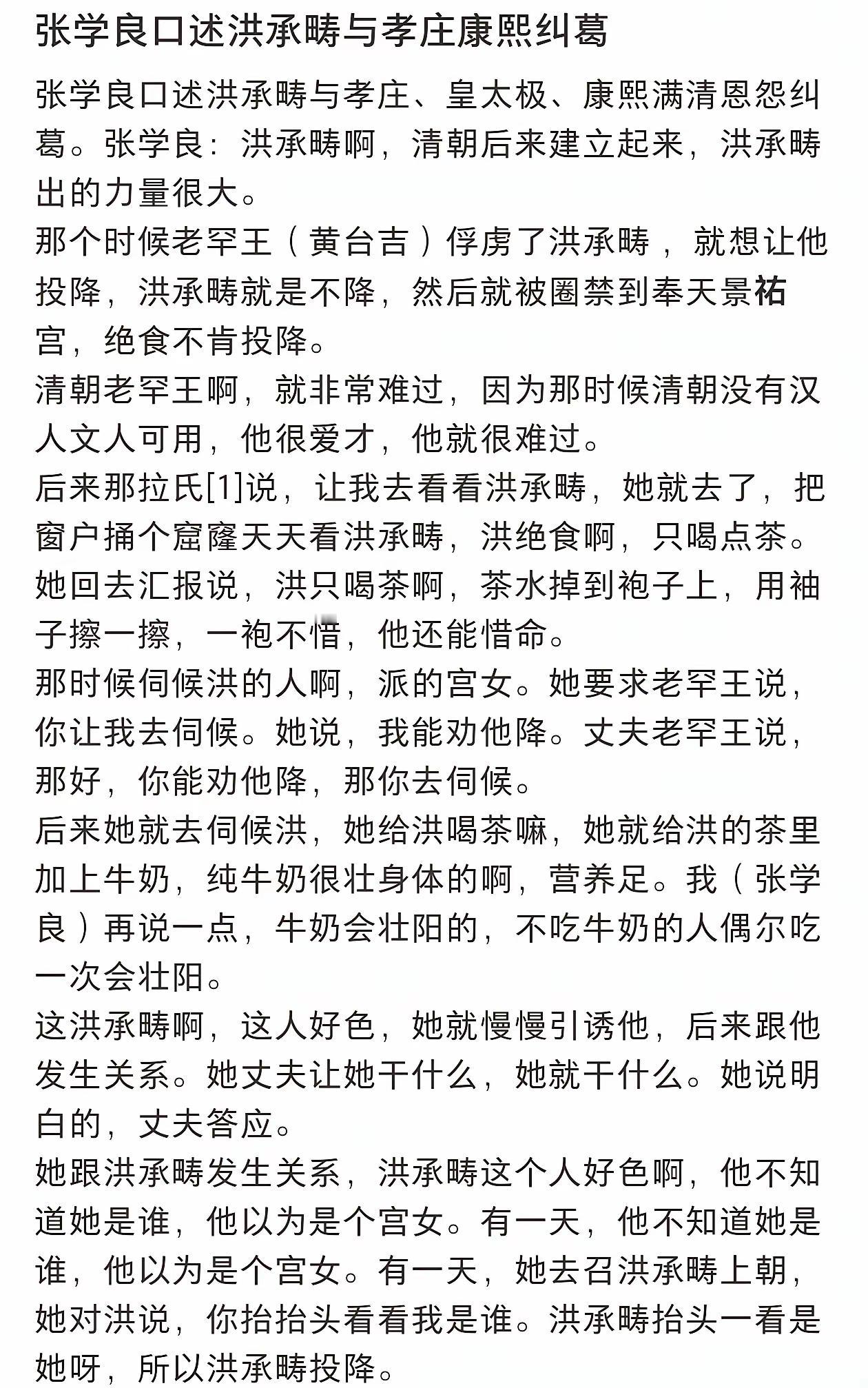1881年,在慈安太后葬礼上,左宗棠怒怼慈溪:“臣前几天还看见慈安太后,身体硬朗,怎么如今就去世了?”身边大臣们听完双腿发软,左公的话说出了所有大臣的心声,也把他自己推向了不幸的结局。 那句话说出口后,礼官的手都僵住,不明白左宗棠为何在这种场合发声。他站在人群前方,声音平稳,每个字都打在众人心里。慈禧站在祭坛位置,闻声后仅停顿片刻,随后继续按礼制行礼,仿佛未听见。 葬礼结束后,军机处大臣接到传话,让左宗棠暂时回府休养。消息传出,很多官员心里明白,这是“远离京城”的前奏。果然第二天,旨意下达——调任两江总督。看似升迁,实则撤离京中,让他不再接触中枢事务。 左宗棠拿到旨意时,没有抱怨,只让随从准备行装。他对亲信说:“在大礼上,我不能装作不知道。” 他是从新疆前线回到京城,慈安太后召见过他,亲自询问边疆事务,用词有条理、精神很好,他对太后的身体状况印象深刻。三天后传出“暴崩”,他第一时间便觉得荒唐。 慈安去世当天,宫门封锁得极紧,外廷只能凭零碎消息判断内情。部分御医在书房被留询,他们说太后突发急症,来不及诊治。消息被压得很死,宫人没有人敢讨论细节。到了葬礼那天,慈禧站在主祭位置,面色冷淡,所有疑点都无法追查。左宗棠当时心头难忍,所以才脱口质问。 左宗棠被派往两江后,事情看似风平浪静,但京中对他的态度变得冷淡。朝廷处理军务时不再请他附议,他送上奏折也常被搁置。他了然于心,却仍然全力处理地方事务。到江南后,他巡视江防,检查水利,还推行军械制造计划。他虽然远离权力核心,却一直紧盯国事。 直到1884年中法冲突爆发,他再度上折请求为边疆出力。他强调若不抵抗,将来外患更重。清廷内部争论不断,他的意见被压在档案箱中。他清楚自己说的话已没有重量,却依然保持以前的态度。他走访军营,查看枪械,安排防御,直到身体越来越虚。 1885年年初,他被任命督闽军务。他拖着病体前往福建,住在行辕里继续处理战事。他耳朵渐背,眼睛昏花,却每天批阅文件。他对同僚说:“若能撑过这个局面,我也算尽力。”那年秋天,和约消息传来,清廷同意结束冲突。左宗棠得知后沉默许久,隔日便递交辞呈,请求归乡。他在福州不久病逝,享年七十四。 左宗棠刚直,不拘礼数,办事说话都较冲,他在慈安健在时深受其赏识,而与慈禧关系历来紧张。慈安去世后,他在礼仪中的一句问话,无疑是在追问死因,这在慈禧听来,是对权威的挑战。她本就忌惮他在西北的军功,担心他在朝廷影响过大,所以借此机会将他调离京城。 而左宗棠并非不懂朝局之险,他知道自己说出那句话会有风险,却难以接受宫中连死因都不能问。相比起安稳,他更看重心里的底线。 他从湘军崛起,到治理新疆,边疆政务多因他而稳。他脾气硬,说话直,但一生为国奔走。葬礼上的那句话,只是他多年性格的自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