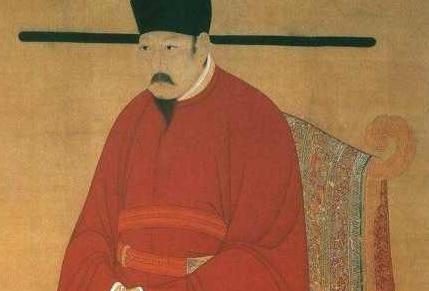张廷玉试探着问乾隆:“臣近八十岁了,可不可以荣归故里了?”没想到,乾隆“唰”得变了脸色,并引经据典说了一句话,张廷玉赶紧跪倒在乾隆面前痛哭流涕。 那是乾隆十三年的正月,紫禁城的红墙在残雪映衬下泛着冷光。七十四岁的张廷玉佝偻着背,朝服上的金线被岁月磨得发暗,他攥着袖中的奏折,指尖几乎要掐进掌心。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是人臣最高境界!”乾隆的声音不高,却像冰锥砸在金砖地上,每一个字都带着寒意。御座上的年轻帝王微微前倾身体,目光扫过张廷玉花白的鬓角,那里还留着康熙朝南书房的墨香,雍正朝军机处的烛痕。 张廷玉的眼泪砸在青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他想起四十五年前,自己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庶吉士,在南书房为康熙誊写密诏,那时候的御案上总摆着父亲张英留下的端砚——父亲是康熙朝的文华殿大学士,桐城张家的门楣就是这样用笔墨和谨慎撑起来的。 康熙五十九年那个冬夜,他从刑部侍郎任上被急召入宫,康熙指着案头堆积的刑案卷宗说:“张英的儿子,该有这般利落。”六十一年,他转任吏部,手里攥着天下官员的升降簿,康熙拍着他的肩膀道:“有你在,朕放心。”那时候的恩宠,像春日暖阳,照得他以为官场这条路,只要谨慎就能走到头。 真正的烈火烹油,是雍正朝的到来。新帝即位当夜,他就被引入养心殿西暖阁,军机处的牌子在烛火下泛着红光。“西北军务、密奏制度、《明史》修撰,都交给你。”雍正的朱批上总写着“甚合朕意”,临终前更在遗诏里写下“配享太庙”——这四个字,是清朝入关以来,汉臣从未触碰到的荣耀。 可荣耀在乾隆这里,变成了枷锁。当张廷玉颤抖着举出杨士奇、徐溥的例子时,他看见乾隆嘴角勾起的冷笑。“宋明之事,焉能比我大清?”帝王的手指轻叩御案,“配享太庙者,当与国同休,你想走,是觉得朕这里容不下你,还是觉得这太平盛世,不需要老臣了?”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张廷玉最后的幻想。他这才明白,自己错把先帝的遗命当成了免死牌,却忘了新帝眼里,所有的“恩典”都带着缰绳。雍正的铁券丹书,到了乾隆手里,不过是一根捆住他的绳索——捆得越紧,越显得帝王掌控全局。 接下来的一年多,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声里,总夹杂着张廷玉上疏的沙沙声。他写自己的老眼昏花,写自己的腿脚不便,写桐城老宅的枇杷树该修枝了。乾隆却只在奏折上批“知道了”,偶尔召见,便指着殿外的松柏说:“你看它们,哪个到了岁数就自己挪窝?” 乾隆十四年的冬天,那道允准归乡的手诏终于递到了张廷玉手里。“皇考成命,永配太庙”八个字,烫得他指尖发颤。他捧着这张“保证书”,对着养心殿的方向叩了三个头,以为终于能带着这份荣耀回家。却不知,这不过是乾隆布下的又一个局——一个让他在希望与绝望间反复挣扎的局。 乾隆十五年二月,北京城的积雪还没化尽,皇长子永璜的丧钟就敲碎了紫禁城的宁静。张廷玉的南归奏疏恰在此时递上,说“祭奠事毕,即辞驾南行”。正在丧子之痛中的乾隆,看到奏折时猛地将茶盏掼在地上:“朕尚在哀戚,他倒急着走——是嫌朕这里的哭声吵了他的还乡路?” 圣旨如冰雹般砸向桐城。历代配享太庙大臣名单被扔到张廷玉面前,墨迹淋漓的朱批质问他:“看看这些名字,哪个不是死而后已?你活着就想归田,是要让后世说朕刻薄,还是说你张廷玉不配这太庙香火?”他吓得连夜上疏,求罢配享,只求留条性命。 可乾隆要的,从来不是他的“请辞”,而是彻底的驯服。伯爵被革去时,他正在整理雍正赏赐的玉如意;追回御赐匾额时,他刚写完给儿子的家书;连女婿朱荃当年匿丧赴任的旧案都被翻出,抄家的差役踹开朱家大门时,张廷玉正在桐城老宅的天井里,看着一只蜘蛛结网。 那几年,张廷玉活得像个惊弓之鸟。京城来的每一封书信,都让他彻夜难眠;地方官路过桐城的每一次拜访,都让他冷汗直流。他捐了十万两银子赎罪,可乾隆的谕旨还是隔三差五送到——有时是斥责他门生在地方“行事乖张”,有时是质问他为何不“感念皇恩,闭门思过”。 乾隆二十年四月,桐城的枇杷树刚结出青果,八十四岁的张廷玉终于在恐惧中咽了气。消息传到京城,乾隆沉默了许久,下旨辍朝三日,恢复其配享太庙资格,谥号“文和”。 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开场时锣鼓喧天,落幕时曲终人散。张廷玉想要的荣归故里,终究成了一场空;乾隆想要的帝王威严,却在他死后,用那道恢复配享的圣旨,轻轻盖了过去。只是没人知道,当张廷玉的牌位被请进太庙时,那冰冷的木头里,是否还留着他晚年的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