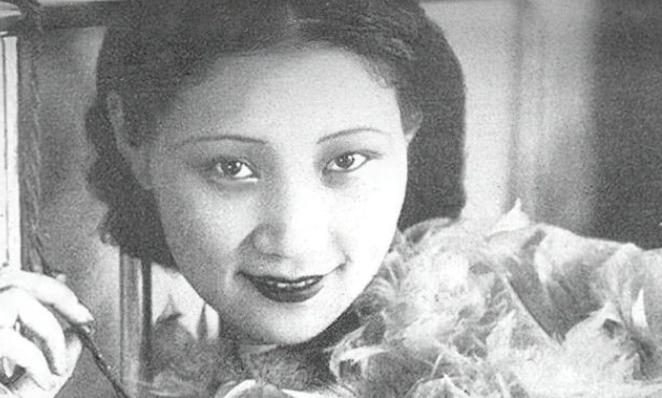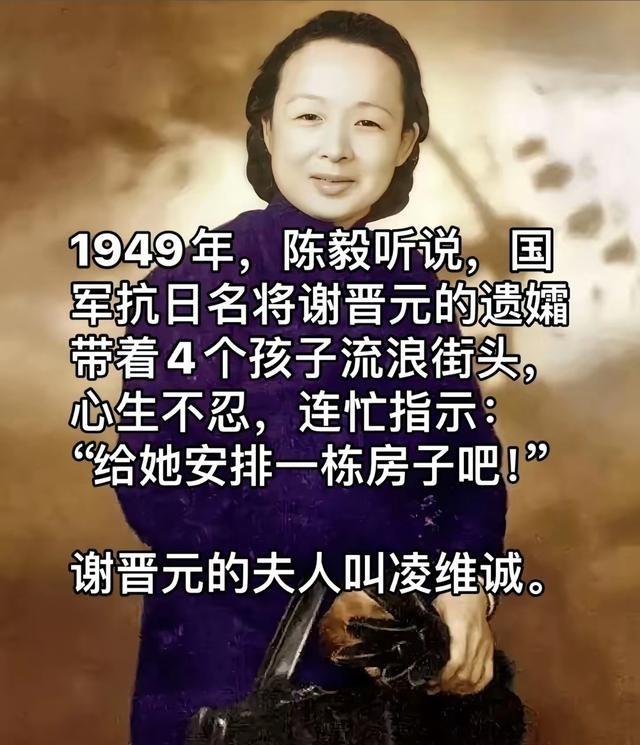1955年的上海,刑场外围满了人。 当那个头发花白、穿着打补丁棉袄的老妇人被押上台时,前排有个抱着孩子的大妈还小声嘀咕:“这么大年纪,犯了啥事儿?”直到审判长念出“钮梅波”三个字,全场突然安静得能听见风吹动标语的声音,谁能想到,这个看着像街坊老妈子的人,竟是在上海滩藏了二十年的双面间谍。 很多老上海人还记得,三十年代的百乐门舞厅里,总有个穿旗袍的女人坐在角落。 她不怎么说话,却能让洋行经理、军政要员主动递名片。 那会儿她还不是“老妈子”,是十里洋场有名的交际花,拒绝过不少权贵的追求,却总在牌局、酒会上恰到好处地“忘记”带走手帕、扇子,这些小物件后来都成了日军特高课的情报。 1941年冬天,上海租界彻底沦陷。 日本宪兵队的高桥少佐带着一箱子金条找到她,说只要她把社交圈里听到的抗日消息透出来,这些都是她的。 她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第二年春天,军统上海站的“夜莺计划”刚启动,7名负责传递情报的志士就被抓了,尸体后来在苏州河下游被发现。 上海市档案馆的老档案里写着,是她在牌桌上套出了接头地点。 日本投降那天,她没跑。 反而拿着一沓日军情报找到国民党军统,说自己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 就这样,她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特务。 1948年申新九厂工人罢工,她假扮记者混进队伍,把罢工领袖的名单交给了保密局,导致3人当场被开枪打死。 我觉得,当一个人把生存的智慧变成背叛的工具,其实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1955年3月,陈毅市长在市政府会议室拍了桌子。 桌上摊着愚园路一栋老洋房的平面图,那里是她藏密写药水和微型相机的地方。 公安干警伪装成送葬队伍,抬着空棺材进了弄堂,在后院地窖里搜出12部电台和300多份情报。 那些情报里,既有日军时期的抗日人员名单,也有国民党时期的工厂复工计划。 审判那天,她站在台上,脸上没什么表情。 直到念到“1943年破坏抗日组织,致7人牺牲”时,她攥着棉袄衣角的手才抖了一下。 台下有个白发老人突然站起来,指着她喊:“我儿子就是那时候没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扔菜叶子的、骂人的,法警费了好大劲才维持住秩序。 刑场上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和愚园路老洋房里凝固的密写药水,都在说同一个道理:把投机钻营当成人生捷径,最终只会被时代清算。 这个曾经在十里洋场呼风唤雨的女人,到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成了耻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