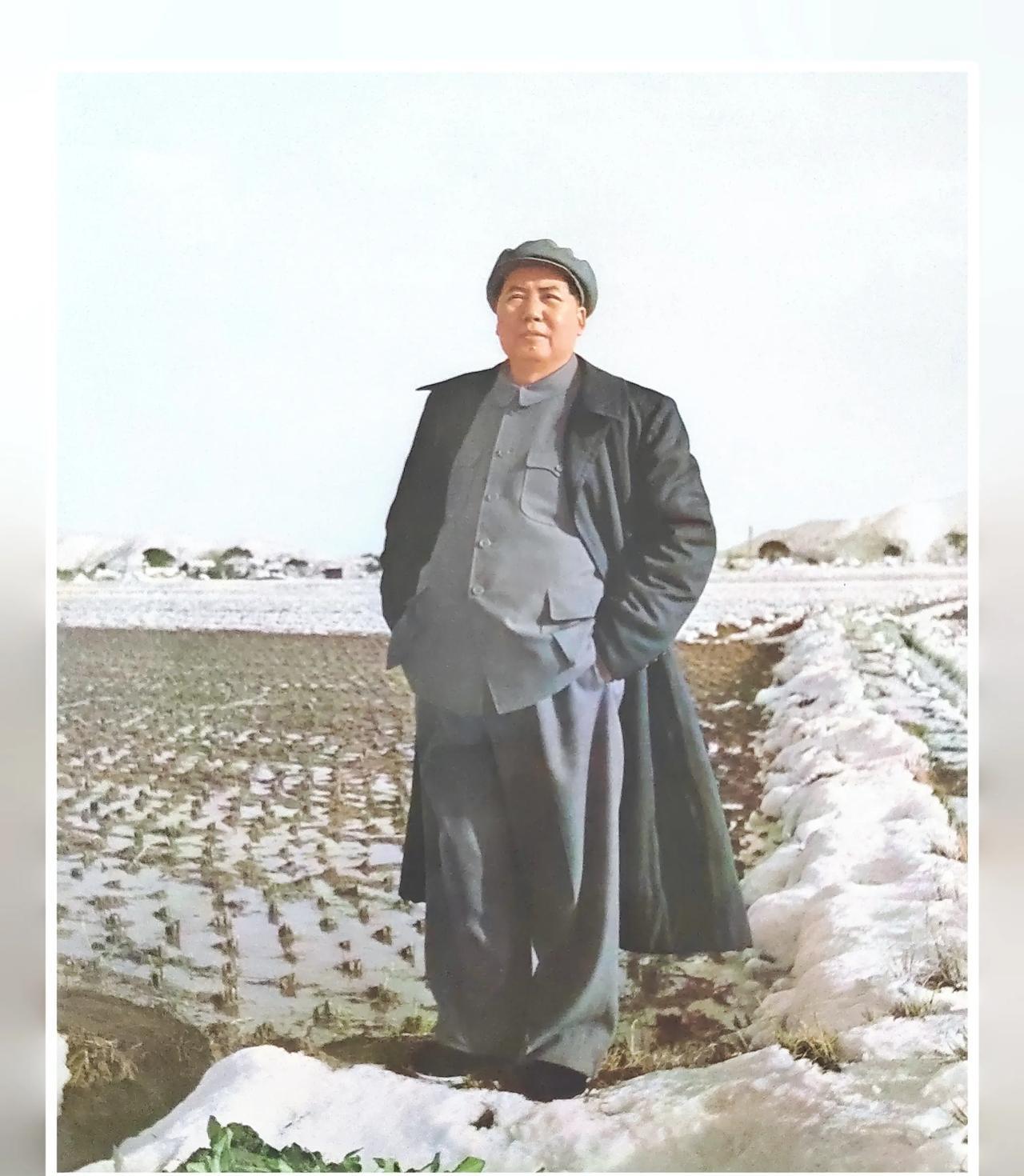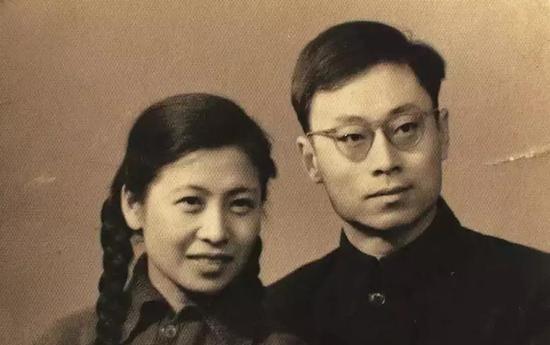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听说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了“香港废青”,“港独”,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那年春天,越战宣告终结,北越军队攻陷西贡,南越政权土崩瓦解。 大批南越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商人乃至普通百姓,在政治清洗和经济崩坏的恐慌中铤而走险,纷纷投奔海外。 越共政府废除旧币、设立再教育营,尤其针对华裔族群展开清洗,许多广府人、潮汕人只因姓氏而被划为“可疑分子”,家破人亡。 逃亡,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于是,从1975年起,无数破船木筏穿越南海,直奔南方一隅的香港。 到1980年,仅仅五年之间,香港共接收了超过10万人,是港英政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民压力。 早期的香港政府尚未准备好应对如此规模的难民潮。最初,这些越南船民被安置在深水埗、漆咸道的军营旧址,帐篷搭起、草席一铺,人们便暂得栖身之所。 彼时的政策尚属开放,难民可以外出打工,很多人参与制造业、清洁行业,为香港经济低端劳动力提供了补充。 然而,随着人数激增,问题开始浮现。1982年,港府正式设立封闭式难民营,芝麻湾、白石等地成为越南船民的集中居所。 这些营地实行封闭管理,难民不得随意外出,生活物资全部由政府提供。看似“衣食无忧”,实则人满为患、秩序混乱、卫生堪忧。 更棘手的是财政问题。每名难民每年耗资约1.2万港元,到1998年,联合国难民署已拖欠香港政府超过11.6亿港元的相关经费,至今未偿。 对于一个本就资源有限、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城市而言,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营区内的生育率也成为一道令人困惑的现象。 由于“出生即有香港身份”的政策诱因,加之封闭环境中缺乏娱乐与出路,家庭观念深重的越南人开始“以生存代替生活”。 据统计,深水埗营区日均新生婴儿数达到3到4人,远高于香港本地平均水平。 在白石难民营,甚至出现同一家庭育有八名子女的极端个案。而这些孩子,日后便成为“香港人”。 1988年,港府在压力之下推行“甄别政策”,将难民区分为“政治难民”与“经济船民”。前者可申请转往第三国,后者则视为非法入境者,予以遣返。 香港电台专门设立越南语广播“北漏洞拉”,向营区宣传遣返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引发了激烈冲突。 1992年石岗难民营骚乱中,因遣返争议,导致2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那一夜,火光冲天,警棍与木棍交织,血迹斑斑,成为香港难民政策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至2005年,20万越南船民中,14.37万人被第三国收容,6.7万人被遣返,只有1,385人最终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 这些少数留下的人,成为了香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后代多数已能讲流利粤语,却始终难以完全融入主流社会。 由于成长背景、教育资源和社会认同的缺失,不少人从事基层职业,如清洁工、外卖员、小摊贩。 也有一些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教师、护士、会计师,甚至艺人,如吕良伟、徐克等人即拥有越南背景。 但也不可否认,在2019年那场社会动荡中,部分越南裔青年出现在街头,参与抗议。有人将其归咎于“忘恩负义”,有人指其“吃里扒外”。 但如果仔细审视这些人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他们并非不知感恩,而是长期边缘化、标签化、缺乏归属感的结果。 这不是某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是一整代人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错位。 1998年,香港正式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2000年,最后一个难民营——望后石中心关闭,标志越南船民历史画上句号。 滞留者中,约1,400人获得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他们散居于香港各区,多从事餐饮、装修、交通运输等行业,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香港大约有15万越南背景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融入社会,子女受教育、就业、纳税,与本地人无异。 他们未必风光显赫,却脚踏实地,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默默耕耘。 这段历史并非仅仅关乎越南船民,更是香港如何在国际义务、人道情怀与本地承受力之间寻求平衡的缩影。 在接受他们的同时,香港承担了沉重的财政与社会成本,面对了治理、治安、文化融合等多重挑战。 但同样,香港也展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法治框架下的制度韧性,和对“他者”的包容度。 信息来源: 《离散越南·回溯丨百年移民路:“不漏洞拉”们的聚散飘零》——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