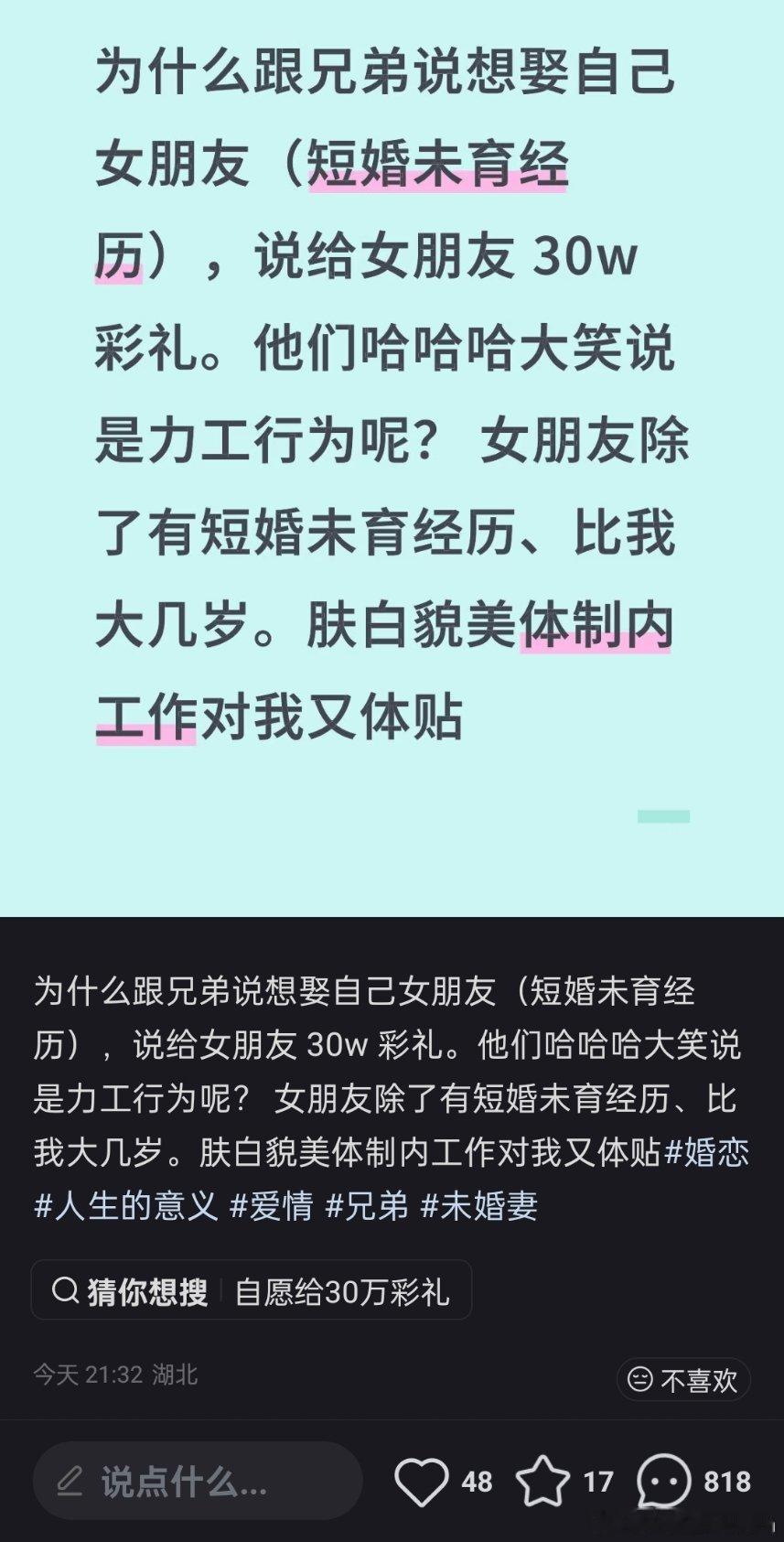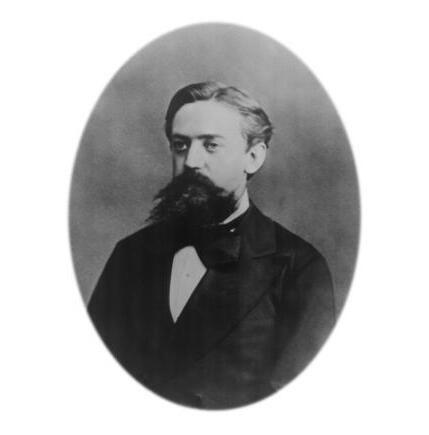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冬夜,十二岁的小管谟业手里捏着张通知单,路过教师宿舍时,一股花生香钻进鼻孔。窗户纸上有个小破洞,他好奇凑近一看,屋里灯光昏黄,男教师正往郑红英裤腰里塞花生,她笑声不断。这一眼,本该是孩子气的偷窥,谁知竟像一颗石子,砸乱了整个求学路。十七年书本断缘,从田间劳作到军营起步,莫言的笔下乡土味儿越来越浓。这背后,藏着多少农村孩子的酸甜苦辣? 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五十年代中期,管谟业出生在个普通农家。家里地薄人多,爹妈起早贪黑,勉强填饱一大家子肚子。他小时候瘦巴巴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冬天冻得手脚发紫。村里没啥玩头,他就爱蹲在老槐树下,听老人讲那些乡野故事,脑子里全是英雄狐仙的影子。小学那几年,是他最亮的日子。土坯教室里,窗户纸透风,他坐在木板桌前,攥着半截铅笔,一笔一划写字。课余借本书,靠墙根看一下午,页边翻得沙沙响。可家是中农成分,这层帽子一扣,学业就卡壳了。十二岁那年,他背起破布包,走出校门,身后黑板字迹模糊,心里空荡荡的。 一九六七年冬天,村里让他去宿舍送通知。那晚风大,路黑,他攥紧纸张,走到近处,花生味儿飘出来,花生那时可是稀罕物。他停步,透过窗纸破洞往里瞧。屋里男教师往郑红英裤腰塞花生,她笑得肩膀抖,花生掉几颗在地上。管谟业脑子嗡一声,赶紧跑回家,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他跟好友张立新说了。张立新一听乐了,从灶灰里抠块炭,拉他到大队部墙前画起来。画上男教师手伸裤腰,郑红英笑得夸张,旁边写着“塞了一斤花生”。村里孩子围上看,大人指点议论,郑红英的名声一下子成了笑柄。她在村口骂了好几天,可风言风语止不住。 这事儿在村里传开,郑红英脸上挂不住。转眼一年,村办起农业联合中学,管谟业满心盼头,穿上旧褂子去门口看名单。黑板上名字密密麻麻,他找半天,没他的。姐姐拉他去找郑红英,她坐在办公室,冷着脸说:“你们家中农,上级不让收。”姐姐低声求情,她看都不看,起身就走。第二天,姐姐带几个鸡蛋再去,她瞥一眼,直接推开:“别拿这个,没用。”门一摔,管谟业站在那儿,低头看地。这条路断了,他回家拿起锄头,加入社员队伍。 辍学后日子苦哈哈的。天不亮就下地,扛锄踩泥路,夏天太阳晒得头晕,冬天风吹手麻。干活歇口气,蹲地头啃冷窝头,嘴里涩味儿冲天。那几年,他跟书本绝缘,只能跟田野打交道。农村的酸甜苦辣,全刻进骨子里。亲戚托关系,他去县棉花加工厂干活。车间机器轰鸣,棉絮飞满屋,他站传送带旁,双手捋棉包,扛到肩上腰酸。休息时,掏出废纸秃笔,借昏灯写点东西。纸粗笔钝,他记下工厂的喧闹和生活碎片。这些字,是他苦中作乐的家伙事儿。 一九七六年,他参军了。穿上军装,踩操场黄土,日子有了规律。早跑步,汗湿帽檐,训练完腿软。闲下来借书看,油灯下翻页,眼睛熬得疼。一九七八年,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他站在报摊前,指划报纸上的字,像做梦。《丑兵》出来后,他提了干,肩章多道杠,走路带风。一九八三年,调到延庆总参三部五局宣传科。办公室翻资料,写东西顺手多了。《民间音乐》刊出,作家徐怀中看中,荐他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课堂上,他捧新本子听课,笔记密密。一九八五年,《透明的红萝卜》上《中国作家》,样刊到手,指尖摩挲封面。次年,《红高粱》面世,书店架上摆着他的书,心里踏实。 莫言的路,走得实打实。从农田到军营,再到文学圈,他没忘根。作品里高粱地、土炕、牛棚,全是乡土气儿。《红高粱》拍成电影,传遍大江南北。二零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他成第一个中国人得主。那天院子里接电话,抬头望天,秋风吹树叶响。他的书《蛙》《生死疲劳》,带着泥土味儿,走向世界。这段经历,说白了,就是我们农村孩子常见的坎儿。成分卡路,意外添堵,但劳动人民有股韧劲儿,坚持下去,总能翻身。莫言用笔写出中国乡土的魂魄,激励后辈投身文艺,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