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高杰的尸体被架在睢州城门,军中一夜未出声。那支他带出关中的劲旅,不再有主帅。而就在几日前,他还与部下饮宴,言笑如常。 城破前夕,他曾托人密信史可法,请求调任,却迟迟未得回音。营中人心浮动,有人传言他将自立,有人私下联络清军。 此时的刑氏站在血迹斑驳的军帐前,失语良久。她知道,高杰不死,别人难安;高杰若存,她也难再立足。这个曾随她在闯营共苦、在南明重建的男人,就此折在了一桌送命酒里。 这一切,起始于两年前的一次突变。 高杰原是闯王李自成的得力干将,自陕西而起,屡战屡胜。他与刑氏本无瓜葛,直到部队被派驻潼关,频繁往来使两人关系愈发暧昧。 1634年冬夜,高杰匆匆入营,一句“闯王已起疑心”,让刑氏警觉万分。她沉默片刻,说了句:“走,要带我。” 她明白,一旦事发,无论她是否情真意切,闯王都不会留她。她也不愿做战马与旗帜后的牺牲品。 隔日,高杰领兵西撤,未向闯营交代一言,直投明军贺人龙麾下。明军收留他,授以实权,刑氏也顺势成为“高夫人”,营务大权逐渐移至她手中。她调兵遣将、赏赐军需,甚至与江北各镇联络协调,逐渐成为营中核心。 高杰战功不断,在抗清战线中屡立战功,但他也因此招致同僚忌惮,许定国、刘良佐等皆暗中排挤他。 1636年,高杰赴睢州议事,被灌酒后中毒毙命。数日后,邢氏被授予临时军权,稳定军心。 南明朝廷最终未能给予她儿子足够的庇护,刑氏不得不四处游说,请托朝中重臣收养,以保其后路。最终,有权臣答应将高元爵收为义子,算是保下一条血脉。 而这一切,如果没有那年夜半的营帐之事,也许不至于如此。 高杰为何转投明廷?他虽骁勇,但知闯王兵权渐紧,猜忌心重。刑氏常年管理闯营钱粮,也察觉李自成对其不再信任。 李自成此时正为扩张大顺筹谋,对旧部要求极严。一旦发现亲信有异动,不论军功,皆冷处。高杰若不自保,结局无异于当年史可法对待反意之将。 而刑氏,是掌握这一切动向的人。她看清了方向,也赌上了命。从偷情到叛营,再到主掌兵权,一连串选择背后,是权力、恐惧与生存意志交织出的灰色道路。 她并非为爱奔走,也未因情迷失,而是在动荡时代中,用最快速度完成身份的转换。这种能力,是战场上最稀缺的生存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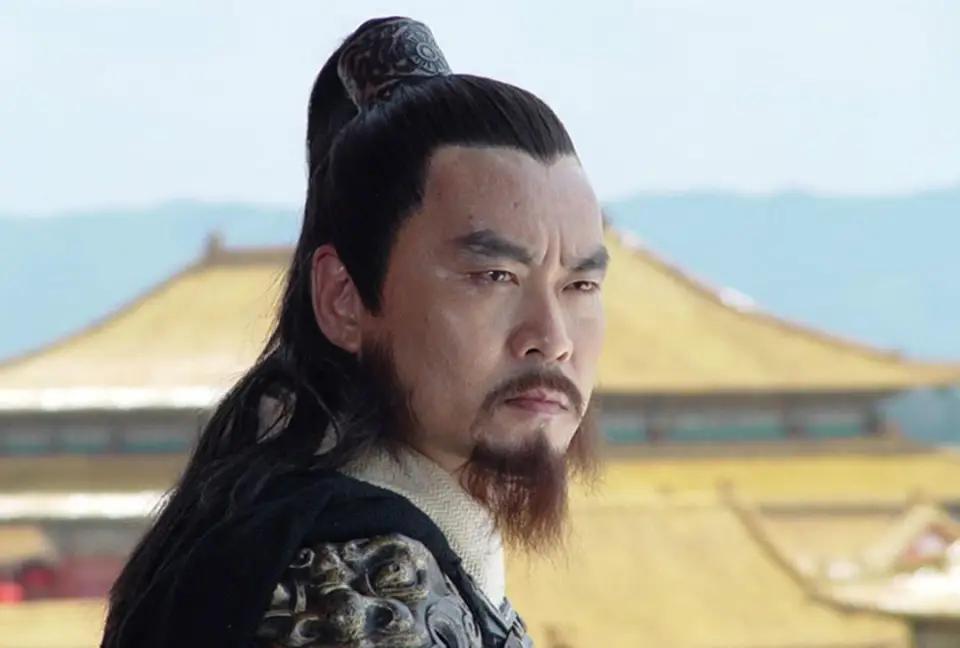

![满清野史想不到明朝最后还给他们种了木马[大笑][大笑][大笑]](http://image.uczzd.cn/4833966861126845595.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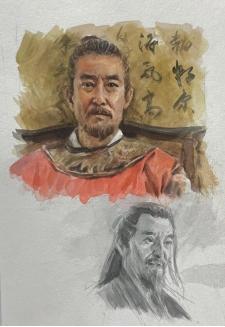

![谁说古代刑法在今天消失了[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2316181724738027723.jpg?id=0)




刘建波
1636年,李自成还没克西安,何来南明?大明亡于崇桢十七年(16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