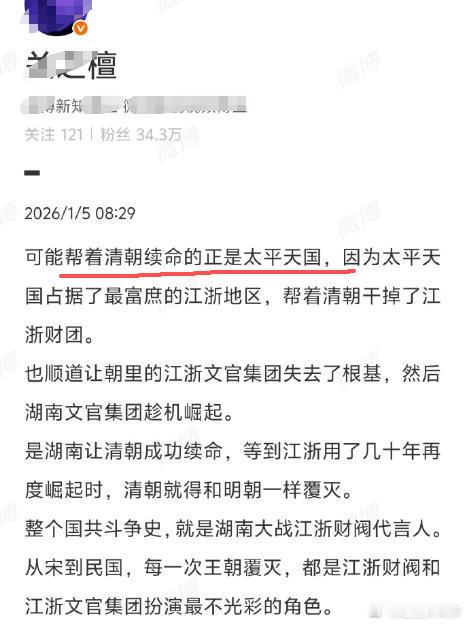有人说‘建这个纪念堂,我是不赞成的,这也并非毛主席的意愿……’我认为这个说法欠妥。如果建成了,没有人去瞻仰,那是真的不妥。但从建成后,每天去纪念堂瞻仰的人群排着长龙,不预约都瞻仰不上!从人民群众踊跃瞻仰看,纪念堂建造能满足大众情感需求,很有必要。 关于毛主席纪念堂,嘴上反对的人不少,脚往那边走的人更多。 广场上纪念堂立在中轴线上,门前队伍一圈又一圈,这些默不作声的脚步,比任何空话都更像一句回答。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午十点,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下午四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响起哀乐,播音员声音发抖念出讣告。厂房关机,课堂停课,许多人站在原地掉眼泪,这股沉甸甸的悲痛往哪去,成了摆在中央面前的现实问题。 最先冒出来的主意很朴素,有意见主张给毛主席找一处山水清秀之地,立一块洁白石碑,松柏环绕,简单庄重。中央却已经决定保留毛主席遗体,用水晶棺长期安放,一块碑承载不了亿万人想要亲眼瞻仰遗容的心愿。 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八地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和工人技师进京,临时组成选址设计组,扛着图板和卷尺四处勘察,在城里城外找合适的落脚点。 纸上的方案一茬接一茬。 选址迟迟拿不定,工作组里气氛压得紧。 负责人顾明,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提起毛主席写给李淑一的《蝶恋花》,那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还有烈士去了“重霄九”、吴刚捧酒、嫦娥起舞,把牺牲和希望放在一处。 纪念堂若只做成阴沉的陵墓,就和这种气度对不上。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中央正式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并宣布纪念堂建成后,把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群众长期瞻仰。 接下来最要紧的问题,是把这座建筑放在哪一块地上,既有象征意义,又经得起现实考验。 故宫午门一度进入候选名单,有人甚至主张拆掉午门,让纪念堂站上去;中南海里的瀛台也被提起,环境幽静,看上去适合作为“长眠之所”。问题在于瀛台所在的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办公区和纪念空间搅在一起,出入都别扭。 越来越多的视线落在天安门广场。 这地方从辽、金时期的古刹,到元大都的“丽正门”,再到明清的“T”形广场,一直是都城要冲。 新中国成立那天,五星红旗在这里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从城楼传向四方。 之后广场整修扩建,北接天安门红墙,南抵正阳门城楼,东连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连人民大会堂,南北约八百八十米,东西约五百米,占地四十四万平方米,成了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决定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范围一划,内部怎么摆放立刻分出几路意见,有的希望纪念堂紧贴纪念碑,有的主张拆掉正阳门让纪念堂搬到城楼旧址,还有人建议让纪念堂紧挨正阳门。 细细一推,问题都浮出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是无数无名烈士,纪念堂面向一位领袖,两者如果粘在一起,各自的含义都会变味;正阳门是北京仅存的完整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南北相对,划出广场边界,还挡住前三门大街车流,从门洞往北看,纪念堂被“框”在中间,这样的景深一旦拆楼就没了;纪念堂若贴得太近,又会在视觉上被城楼压住。 多方权衡之后,正阳门保留下来,纪念堂被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之间的中线上,两头各退开二百米左右,大致落在旧日中华门一带。接下来,是掂量体量和高度。 设计组一开始容易被感情推着走,图纸越画越大,南京工学院的杨庭宝提出边长五十米的正方形方案,像是一句提醒。 负责总体设计的沈勃,在各方意见之间反复打磨,用一整夜画出实施草图,最终定下长宽各一百零五点五米的正方形建筑,对称布置,南北各三扇大门,中轴线甬道穿过高柱,人流顺畅,形象稳重。 高度和标高经过细致计算,站在天安门城楼下和金水桥边看过去,纪念堂既能遮住正阳门屋脊,又不压住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定为三十三点六米;从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两公里地面一共升高三点一二米,在广场上正阳门北洞到纪念碑平均坡度约百分之二,纪念堂标高比原地面抬高一米,从纪念碑到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到台阶以约百分之九的坡度上升,南侧小广场多出来的几级台阶,让建筑更显挺拔。 还有一个常被提起的细节,是纪念堂正门朝北。 中国许多建筑习惯坐北朝南,这次反着来,有人担心广场开大会时,群众朝着天安门城楼,不自觉就把背对向纪念堂。设计组的赵鹏飞提出,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腾出更宽的东西向广场,大型集会时,人群围在四面,纪念堂落在群众中间,“背对”的别扭就淡下去 从九月九日那一声哀乐,到十月八日的修建决定,再到十一月六日的具体选址,还有之后对每一米长度、每一度坡度的反复推敲,这座纪念堂的来历,很难一句“是不是合毛主席本意”说清。 更直观的是,天安门广场门前长龙年复一年,从清晨排到中午,队伍里的每一双脚,都在替那个秋天没说完的话,补上一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