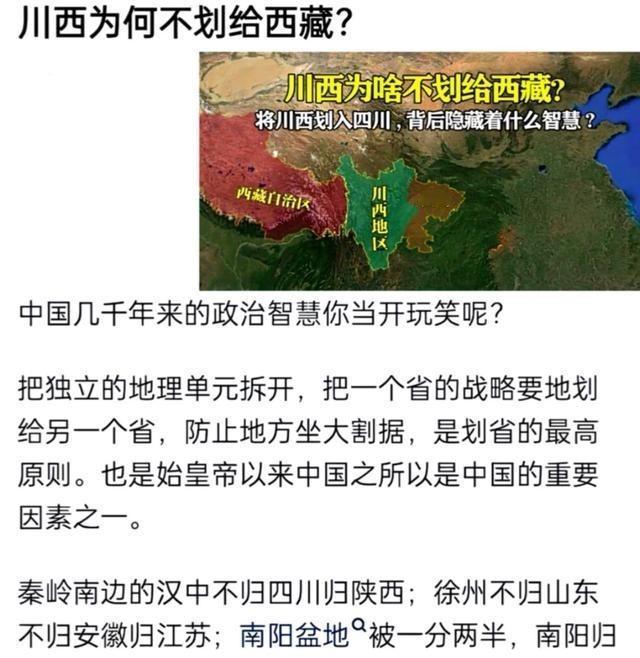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深处,生活着一个特殊的族群——哈扎拉人。他们身着特色服饰穿梭在山谷间,黄皮肤、黑头发的容貌,与周边高鼻深目的族群形成鲜明反差,仿佛是镶嵌在中亚土地上的一抹东方印记。这个总人口近八百万、在阿富汗位列第三的民族,千百年來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他们的根在中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是流淌着东方血液的中国人后裔,这份刻在血脉里的认同,即便历经战乱与歧视也从未消散。 哈扎拉人的东方渊源,并非口耳相传的虚妄传说,而是藏在历史脉络与文化基因中的实证。这段渊源的起点,最早可追溯至盛唐时期的西域经营。公元七世纪,大唐国力鼎盛,为守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先后设立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势力范围直抵今日阿富汗境内。当时的朝廷在阿富汗多地设置都督府,其中哈扎拉人如今聚居的巴米扬地区,正是当年写凤都督府的所在地。大批唐朝军人、官吏、商人和手艺人沿着丝绸之路奔赴此地,戍边、屯田、经商,在这里落地生根,与当地突厥、波斯族群通婚融合,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最初的东方血脉。 安史之乱后,大唐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掌控,留守的中原后裔与当地族群彻底相融,而六百年后,另一股东方力量的到来,彻底塑造了哈扎拉族的族群格局。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挑衅引发了这场震撼世界的远征,阿富汗作为花剌子模的核心领地,成为蒙古大军的重要征战区域。平定此地后,成吉思汗并未撤军,而是留下大批军队驻扎镇守,这些军队以蒙古“千户”为编制,成为守护这片土地的核心力量。 “哈扎拉”一词在波斯语中意为“一千”,正是源于蒙古军队的“千户”编制,这一名称本身就是那段历史最直接的注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蒙古驻军并非纯蒙古人,而是融合了中原金国、西夏、南宋的汉人军士,以及其他被征服族群的士兵。这些汉人军士不仅善战,更擅长农耕、冶炼、建筑等技艺,成为维系当地生产生活的重要力量。当蒙古大军主力继续西征或班师回朝后,这些留守的“千户”部队便就地解散,与此前定居于此的大唐后裔、本地族群再度融合,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哈扎拉族。 文化与基因的双重印证,让哈扎拉人的东方认同有了坚实支撑。尽管如今哈扎拉人主要使用波斯语方言,但语言中仍保留着数百个蒙古语词汇,成为族群渊源的“活化石”。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深深刻着东方烙印,爱吃牛羊肉、饮奶茶,居所是类似蒙古包的圆顶建筑,传统节庆中的诸多仪式,都能找到蒙古文化与中原习俗的影子。现代基因检测更给出了科学答案,哈扎拉人Y染色体中,大量基因序列与蒙古族、汉族人群高度吻合,印证了他们与东方族群的血脉关联。 然而,这份独特的东方基因,却让哈扎拉人在阿富汗的历史中饱受磨难。阿富汗主流族群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而哈扎拉人信奉什叶派,宗教信仰的差异叠加与众不同的东方面孔,让他们长期被视为“异类”,遭受歧视与压迫。尤其是近代以来,阿富汗战乱频仍,极端武装势力的迫害更是让哈扎拉人陷入水深火热,部分极端分子甚至以“种族清洗”相威胁,逼迫他们“回到东方老家”。 这句充满恶意的逼迫,反而唤醒了哈扎拉人更深切的祖地认同。他们虽从未踏足过遥远的中国,却从祖先的传说、血脉的记忆中,将中国视为心灵的归宿。在战乱最频繁的岁月里,不少哈扎拉人高举象征希望的旗帜,高喊着回归祖地的诉求,渴望能回到这片血脉起源的土地,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中国”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承载着族群记忆、给予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千百年的风沙未能吹散哈扎拉人与东方的联结,战乱与歧视也未能磨灭他们对祖地的向往。从大唐戍边将士的坚守,到蒙古千户部队的扎根,再到如今哈扎拉人对回归的渴望,这段跨越千年的血脉羁绊,见证着中华文明对周边地区的深远影响,也诠释着民族认同的强大力量。哈扎拉人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更是一曲关于血脉传承、心灵归依的动人篇章,让我们看到,无论相隔多远、历经多少沧桑,刻在血脉里的根脉,永远是指引族群前行的精神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