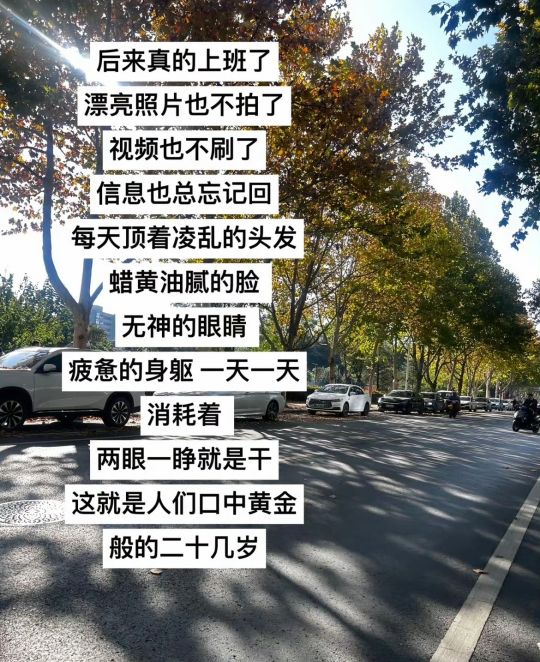在我八岁的时候,独自去了姑姑家拜年,姑姑在暗中给我兜里揣了两角钱,我当乐的不知所措,因为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得到拜年钱,当时我就想好了,等商店开门的时候,这两角钱正好买一挂小鞭炮放着玩,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小手一直按住兜里的两角钱。 那会儿天还灰蒙蒙的,风有点凉,我踩着冻得发硬的土路往家走,脚底咯吱咯吱响。 两只手轮流捂着裤兜,生怕一松劲儿,那两角钱就飞了似的。 其实兜口缝得挺牢,可我心里总觉得它轻飘飘的,像片纸,又像只小鸟,稍不注意就要扑棱棱飞走。 路过村口老槐树底下,碰见隔壁家二蛋,他正蹲着玩弹珠,抬头看见我,咧嘴一笑:“嘿,发财啦?” 我没吭声,只是把兜按得更紧了些,脸有点热,倒不是害羞,是怕他伸手来摸——那钱还没焐热呢,哪能让人碰? 走到半道上,我忽然听见“啪”一声脆响,回头一看,是邻居家小孩点了一串小鞭,红纸屑炸得满地都是,硝烟味儿直往鼻子里钻。 我站那儿没动,耳朵嗡嗡的,心也跟着跳快了几下。 原来两角钱真能换来这么响、这么亮、这么带劲儿的一声啊。 可等我走到村东头小卖部时,铁卷帘门还锁着,门上贴着张纸条:“初一上午不开门”。 我趴在玻璃上往里瞅,货架上果然摆着几挂小鞭,红红的,卷得整整齐齐,像一截截小火龙。 我数了三遍,确认它们都标着“贰角”。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照在脸上暖乎乎的。 我站在门口没走,就那么站着,手还按在兜里,可心里头那股急劲儿,不知怎么就慢慢松开了。 后来我转身往回走,没再想着那挂小鞭,反而想起姑姑塞钱时,手指头有点糙,却轻轻擦过我腰侧的棉袄;想起她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糖水蛋,蛋黄软软的,糖水甜得刚好;想起她说话时眼角的笑纹,像被风吹开的涟漪。 到家后,我把那两角钱掏出来,放在炕沿边的小木匣里——那是我攒糖纸和玻璃珠的地方。 钱是硬币,一面印着麦穗,一面印着国徽,冰凉,但捏久了,也有了点体温。 后来常想,要是那天小卖部开了门,我会不会真把钱递过去?大概率会的吧,毕竟那“啪”的一声脆响,在八岁的耳朵里,比什么都诱人。 可偏偏没开门。 那扇紧锁的卷帘门,像个沉默的老师,逼着我把攥紧的手松开些,往更深的地方看——姑姑递来的哪是钱?是她起早煮糖水蛋时的热气,是她眼角笑纹里藏着的惦记,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普通长辈能给的全部温柔。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两角钱从来不是为了买什么。 它是一把钥匙,第一次把我心里那扇门,悄悄拧开了一道缝:原来被人惦记着,是这种感觉;原来一点心意,可以轻得像羽毛,又重得让我一路护着它走回家。 现在我给孩子压岁钱,从不塞进红包就完事。 我会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这钱你收着,想怎么花都行——但记得,给谁花,比怎么花,更重要。”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已经伸过去抓了。 我笑着,没拦。 就像当年姑姑没拦着我把钱攥那么紧一样——有些懂得,总要等风把硝烟吹散,等阳光把冰土路晒软,才能慢慢长出来。
在我八岁的时候,独自去了姑姑家拜年,姑姑在暗中给我兜里揣了两角钱,我当乐的不知所
小依自强不息
2025-12-08 13:20:46
0
阅读: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