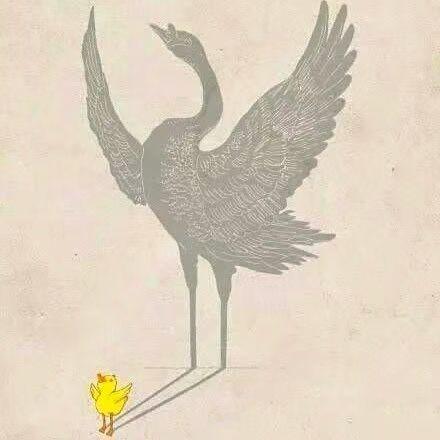“砰”一声,新婚的房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一个黑影冲进来,直勾勾地盯着炕上光着膀子的我,和我身边只穿着小背心的新嫂子。 那年我12岁,是被刚结婚的大柱哥塞了一把喜糖,派来给新嫂子“壮胆”的。他出差,嫂子一个人怕。 夏天的夜里闷得出汗,新房里全是新木头和香皂的味儿。我俩刚睡熟,就被那阵疯狂的踹门声给砸醒了。 门轴断裂的脆响之后,就是死一样的寂静。 那个男人就站在那,不说话也不动,一双眼睛空洞洞地扫过新嫂子吓白了的脸,扫过我攥紧的拳头,最后停在墙上那个大红的双喜字上,整个屋子只有我俩牙齿打战的声音,和我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是该尖叫,还是该抓起床边的枕头。 就在这时,院子里突然炸开一片嘈杂的脚步声,好几道手电光柱晃了进来。 “在这儿!” 几个人影冲进来,一把就将那个男人死死按在地上。他没反抗,任由人拖了出去。 带头的人,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冲着炕上发抖的我们连连作揖:“对不住,对不住,吓着你们了……” 我们这才知道,那是村东头一个精神失常的病人,趁家人没看住,自己跑了出来。 有人说,那是一场虚惊。 但那几分钟凝固的寂静,那个男人投向大红喜字的眼神,成了我后来很多年,关了灯就不敢闭上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