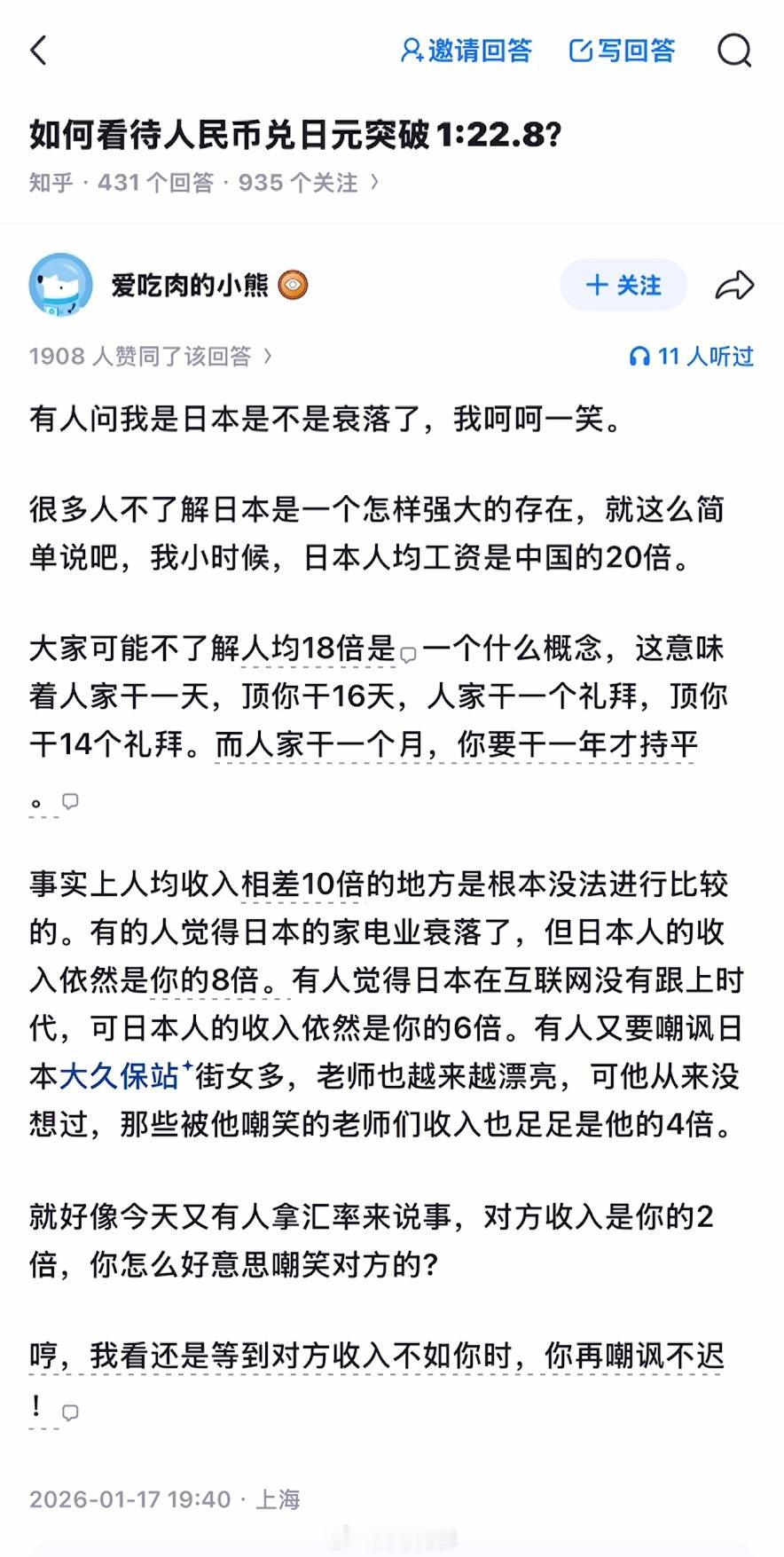一次,陈佩斯的大孙子忘带作业去学校,儿媳妇大声呵斥他说:“作业忘带了也不说,没写也不说,你还有心思学习吗?”看到自己的大孙子被责罚,陈佩斯立马不高兴了!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客厅,斑驳地落在旧木地板上。藤椅里,陈佩斯翻着一本老相册,跟儿子陈大愚一边喝茶,一边聊起当年春晚的日子。 从《吃面条》到《羊肉串》《主角与配角》,那些让全国观众笑到肚子疼的小品,在他嘴里成了轻描淡写的几句回忆。陈大愚时不时接上一两句,把话题从舞台扯到家史,父子俩像老友一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屋子里静静的,很暖。 忽然,一阵尖锐的嗓音从另一边传来:“这么重要的作业你都能忘?怎么回事?” 是儿媳在训大孙子。十来岁的孩子低着头站在原地,肩膀一抖一抖的。 陈佩斯下意识停了话头,合上相册,视线越过半开的门,落在孙子身上。那眼神里有皱着的眉头,也有压着的心疼。 陈大愚看出了父亲的心思,笑着打圆场:“爸,我媳妇说得挺对。当年我忘带作业,你教训我比这重多了,打手板、罚站,可一样没少。” 陈佩斯点点头,嘴上认同“该管就得管”,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想起自己儿时犯错,被父亲训斥时,是爷爷第一个站出来挡在他前头。那种被护着的感觉,一直记到现在。 这一幕,对他并不陌生。 儿子结婚后曾明确说不打算要孩子,那时候,他从春晚舞台退下来,最大心愿就是早点抱孙子。于是软磨硬泡整整6年,从不动声色地“暗示”,到不厌其烦地“催生”,终于等来了如今家里这四个小家伙。 自打有了孙辈,他整个人像又年轻了一轮。平时排戏、写本子之余,三分之一时间在剧场,三分之二时间在围着孩子转。 早上六点多起床蒸馒头,七点叫孙子孙女起床,还要挨个检查书包,生怕谁把作业落下;放学不放心校车接送,就自己开车去学校门口,车后排还装着四个儿童安全座。 周末,他宁可推掉应酬,也要带孩子们上山下河,摸泉水、捡树叶、抓鱼虾,把自己小时候那些“野路子”的乐趣,重新铺在孙辈的童年里。 在他看来,学习重要,但快乐更重要。他当年给陈大愚立的规矩,就是“60分够用,别把自己读成只会考试的人”。现在轮到孙辈,他比谁都怕孩子被压得喘不过气。 刚才那一顿责骂,他嘴上说“儿媳做得好”,其实全程竖着耳朵,生怕火候过了。 没过多久,儿媳因为工作要出差,临走前专门把陈大愚叫到一边,交代要盯紧孩子,忘带作业这种事不能再发生,有错就得罚。陈大愚一口答应,还当着父亲的面半开玩笑:“要是再不长记性,打打手板、少吃一顿晚饭也正常。” 话刚说完,陈佩斯脸立刻沉了下去:“你敢动我孙子一根手指头试试?” 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对儿子,他仍然坚持当年那套“犯错要承担后果”的原则;对孙子,他却本能地想护在怀里。三代同堂的屋子里,规矩和偏爱,就这么赤裸裸地撞在了一起。 陈大愚愣了一下,随即又笑笑没再顶嘴。他其实很清楚,父亲年轻时教自己有多“狠”,也更懂当爷爷以后,那份突然涌出来的心软有多真。 晚上孩子写作业,陈佩斯照旧搬个小板凳守在桌边,遇到不会的题,他翻出旧书耐心讲解。等孩子犯困了,他比谁都心疼,恨不得替孙子把题做掉。 然而真到孩子忘带作业、被老师批评,他又不得不忍住心疼,嘴上跟着一起说“该记住的教训要记住”,只是眼神总忍不住往孙子那边飘。 他越来越明白,当年自己那个总爱替孙子挡着的爷爷,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 一边是儿媳坚持的严格管理,一边是自己骨子里“孩子开心最重要”的信念,中间夹着的是儿子这个正在学着当好父亲的人。三代人围成一个家,关于怎么爱、怎么管、怎么放手的讨论,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 那天晚上,孩子罚站结束,躲回房间偷偷抹眼泪。陈佩斯走过去,没多说教,只是轻轻拍了拍孙子的肩膀,让他赶紧睡觉。转身回到客厅,他又把儿子叫住,慢慢地讲起自己小时候犯错、被训斥、再被爷爷护住的故事。 “规矩不能少,”他说,“可他还是个孩子,挨骂的时候,总得有个地方能躲一躲。” 灯光下,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舞台上的喜剧大师,在家里,只是一个固执地护着孙子的老爷子;那个曾被他打手板的儿子,也开始学着在严厉和心软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而那间老房子里,关于爱与教育的拉扯,还会在许多平凡的下午,一次次重演。



![我去!原来是都偷偷的回来了?是不是因为那根线比较有杀伤力啊![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5924036626146146430.jpg?id=0)